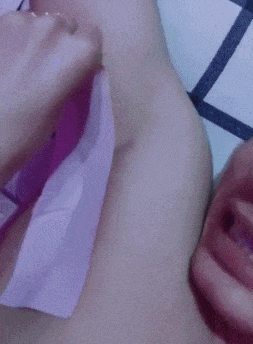走近苏州 走进古典

人文重点:苏州昆曲、评弹、玉雕、琴笛等
人数:40人
苏州文化之旅大事记
12月19日 入冬之际到苏州,不看园林看古雅。青睐人文寻访团一行40人在北京南站乘坐G117次列车,15点05分抵达苏州北站。
12月20日 慢书房。上午9:00,张凌平、唐蔚羽夫妇做评弹讲座。下午1:30,周秦讲授昆曲。两场纯粹的苏州艺术讲座使人迷醉,想象中的苏州就是如此的古润风雅。晚间游走老街平江道,一部分团员到翰尔评弹社继续观赏张凌平、唐蔚羽的评弹表演。
12月21日 上午9:30,蒋喜玉雕讲座,下午参观苏州博物馆,幸遇“贵潘”展。晚上与刘刚、李冬君老师游览苏州老城门。
12月22日 游览昆山千灯古镇,瞻仰顾炎武故居。下午参观太仓考古现场,张志清博士除带我们参观讲解太仓考古现场外,还破例带大家到考古工作办公室参观,令团员们大开眼界。同步观看直播的网友也过足考古瘾。晚餐时会员们即兴表演。
12月23日 上午9:00,俞飞、俞兰璟父女同场,琴笛奏出绝响之音。下午乘坐G142次列车返京,20点18分到达北京南站。
时晴时雨的氤氲苏州,浸润着浓厚的文化气息,迷醉了一众向古的心灵。
文/本报记者 王勉
昆曲
“最早看戏的那些孩子已经进入中年”
周秦
中国昆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戏曲研究教授
昆曲研究专家周秦开讲前,活动总策划刘刚先做开场白:2008年我在昆曲博物馆买了周秦老师的《苏州昆曲》一书。周老师的文字像昆曲里的水磨调,行云流水,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周老师的昆曲是文人昆曲,是吟诗的调子。
刘刚老师的开场白让我们对安静坐在讲台前的周秦老师充满好奇。周秦老师是地道苏州人,吴侬软语的滋养使周老师开口即像吟诗。他说他很高兴在一家小小的书店里和北京来的朋友聊一聊苏州最重要的文化。在他心目中,苏州这座最古老的古城留下了很多重要的文化,物质文化类的园林和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的昆曲、古琴、缂丝等,还有工艺类的苏作,都深深地篆刻着苏州的文化铭牌。
虽然只有短短两个小时,周秦老师和我们分享的昆曲讲座却给了我们高密度的知识含量。他知道团员们都不是昆曲专业,所以不谈很深的道理,而是从昆曲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牡丹亭》讲起,时而娓娓道来,时而击节而歌,讲者专注,听者微醺,一场高水平的讲座实在无过如此。
周秦老师首先谈到,昆曲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整个明朝都是昆曲创作的传奇,其中最优秀的包括元朝的《琵琶记》、明朝的《牡丹亭》和清朝的《长生殿》。这三部也是周秦老师要求他的硕士研究生字字句句从头到尾读通的,“我们的学生有这个本事。”
《牡丹亭》是明朝江西临川(今抚州)人汤显祖的剧本,写于1598年,2018年正好是420年。汤显祖笔下的剧本怎么唱红了舞台?周秦老师说:“那是用昆曲唱红的。”
周秦老师强调,昆曲和京剧等其他戏曲不同,昆曲是雅部,京剧和其他剧种是花部。雅部重视的是书面上的文学和音乐,是用来言志抒情的;花部注重舞台上的表演,是用来娱人的。所以在文化市场上,昆曲比不过花部的戏,因为花部戏好看,层出不穷,但是从文化价值上是不能和昆曲相比的。
“昆曲的每一句唱词、每一个音符,都可以找到文献依据,所以昆曲没有流派,只有对和错。”周秦老师说,昆曲有2000多个曲牌,每一个曲牌都是不同的音乐框架。“大家看这一段唱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好美!这是明朝最了不起的作家写的最美的词。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游春兴高采烈,不是的,它带着淡淡的哀愁,引发我们对生活对生命的思考,很淡雅,像刚下过雨的苏州古城。这是中华民族最高境界的美。当然,如果配上音乐,那就更美了。”
很多人都知道,汤显祖把《牡丹亭》写了五十五出,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冗长的爱情故事呢?周秦老师谈到汤显祖的一段题词,“汤显祖写完《牡丹亭》后就辞官回家了,写了一段挺长的题词,其中一句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周秦老师认为,这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杜丽娘死而复生,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但现实生活中不可有,文学艺术中不可无,这是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生活的理想。一个人如果没有点浪漫精神,没有一点点对生活的念想,那是行尸走肉。同样,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点浪漫精神,没有点对明天的向往,也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好在我们中华民族一向都有滔滔不绝、源源不断的浪漫精神。”
周秦老师说:“大家可以想象,400年前,《牡丹亭》对于有了些文化却又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女孩子的冲击。学历史的人都知道,资本主义萌芽是以苏州为中心的纺织工业发展起来了,随之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继而出现的是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是人类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个觉醒我们和西方是同步的,我们叫它资本主义萌芽,西方叫它文艺复兴时代。”
汤显祖生于1550年,卒于1616年,这也正是世界文明发展的辉煌时期。“我们可以看到,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比汤显祖大3岁,英国的莎士比亚比汤显祖小14岁,很有意思,这三个人不是同年生,却是同年死。所以汤显祖在写《牡丹亭》的时候,莎士比亚差不多在写《罗密欧与朱丽叶》。”周秦老师说:“相比之下,杜丽娘的觉醒和浪漫要强过朱丽叶,我们的杜丽娘更执着更浪漫。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思想。”
之后,周秦老师谈到青春版《牡丹亭》创作演出的前后过程,缘起是他的老朋友白先勇。
两个人是老朋友,1992年即已相识。那时周秦像唐·吉坷德一样撑着全国唯一的一个昆曲班。2003年白先勇再到苏州,来和周秦商量打造青春版《牡丹亭》。“这在当时是有争议的,因为一说青春版,大家就以为是改革的。白先勇对我说:‘周老师,你别固执,现在孩子们受到的诱惑太多了,酒好也怕巷子深。’他说得有道理。我曾经把最好的梅兰芳、俞振飞版《牡丹亭》给学生看,他们不爱看,说不美,像老头老太谈恋爱。就这一点白先勇把我说动了,那我们就试试。”
困难当然很多。周秦老师谈到,首先,遗产意义上的《牡丹亭》昆曲有11出,情节不连贯,要打造,便先要对剧本进行整编,“不是改编,是只删不改,保留原本。”周秦强调。最终,他们将《牡丹亭》打造成了方便大家看懂的“梦中之恋”“人鬼之恋”“夫妻之恋”三个层次,整编后的本子也要演3个晚上9个小时。
白先勇亲自挑选了他心目中的杜丽娘和柳梦梅。之后,他请来多年不出台的昆曲老艺术家亲自教授两位年轻演员,周秦任唱念指导。“会唱了以后带他们到我家,一点一点,告诉他们什么是如花美眷,什么是似水流年,如何进入戏曲,如何感动观众。”
青春版《牡丹亭》首演剧场选在台北国家大剧院,排练在苏州。“苏州当时还没有大剧院,白先勇有办法,租了一个烂尾楼,现在是万豪国际大酒店,把一半变成和台北国家大剧院一样的舞台,在那儿演。”白先勇请周秦去看,周秦没租大巴士,他带着八九十名学生骑自行车穿过苏州古城,连看3天6场18个小时,没有学生中途离开。“白先勇很得意,说我们成功一半了。”
台湾的票提前三个月全部卖完,买票的很多是还在读书的孩子,三场演出后好评如潮。“之后白先勇带着剧团继续巡演,到处打电话给我。香港那次电话我记得最深了:白先勇激动得嗓子都哑掉了,他有点口吃,先叫周周周周先生,我拖个椅子坐下来听,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告诉我在各地怎样受欢迎。我问我们的演员稳住了吗?他说,稳住了!我好高兴!”
之后,6月中旬开始内地巡演。首演在苏州大学,也是白先勇选的。从上海到北京,从武汉到广州,周秦他们所到的高校集中区,场场爆满,这也坚定了白先勇以高校为基础推广昆曲的理念。
再后来走出国门,不懂中文的老外也爱听爱看,“记忆最深刻的是在洛杉矶,演出完全场老外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整齐的哗哗声,像海潮一样,一浪高过一浪,非常震撼。他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中国艺术的敬仰。”
第200场公演在国家大剧院,周秦说:“白先勇情绪有些低落,他说我们九年了,还是没有看到什么。我说我们值啊,我们把几十万大学生引进了昆曲剧院里。白先勇说,值是值,但是这两百场我们投下了3000万元,血本无归。这些都是我朋友的钱啊,从明天开始,我不知道我这张老脸再向谁开口要钱。另外,我是一个作家,生命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得回去写东西。”
“之后我们便主要自己做,尽量少麻烦白先勇,只是和他谈我们的演出又怎么样了。他会说,要爆满,要爆满。”200场演出后的《牡丹亭》变成了一个品牌,无论到哪儿,场面都非常好。“所以,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自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很优秀。14年,我们演了320多场,几十万高校师生看了我们的演出,最早看戏的那些孩子现在已经进入中年。凭这一点,我们的昆曲50年死不了。50年之后怎么办?要靠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来努力。”
2013年时,《牡丹亭》首演快要十年了,白先勇到来苏州找到周秦,请周秦帮他做三件事,他想看三个地方,一个是忠王府的古戏台,他在那里挑选的演员;第二是沧浪亭,苏州有108个园林,最古老的是宋代的沧浪亭,他曾在这里给孩子们讲苏州文化;第三是到苏州大学看看首演的地方。“当天他走进空无一人的大礼堂,走向舞台。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在舞台上他滔滔不绝地讲,直到他的秘书提醒他该走了。”
周秦老师的讲座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李冬君老师有些激动地说:“周秦老师,非常荣幸,那时我在南开大学,你们在那儿的演出我和刘刚都非常有幸地看了。感谢你们这些年来为昆曲所做的一切。”团员们更是纷纷询问苏州哪里能看到《牡丹亭》,周秦老师热情地掏出手机说:“我来帮你们安排!”
文/本报记者 王勉
本版摄影/木头
回到古典中国
李冬君(文化学者、青睐人文寻访苏州行总策划)
走进苏州,便来到了古典的天堂。
“古典”与“古代”不同,“典”指经典,指在泥沙俱下的历史长河中鼎出的各种具有永恒性的文化范式;而“永恒性”,则指人类为自己创造的符合人性的、滋养人类心灵的精神品,它必须具有审美意味。
凡是物化的总会被时间磨损,或被新技术取代;凡是古代意识也会被人类不断地自我认识所更新,因此,古代是历史的过去式,是人类在试错中成长的见证。有时间摘取“经典”时甩掉的粗糙不堪,也有令人凭吊的扼腕感叹,这便是“古代”的品相。
南派笛箫丝桐,以苏州为重镇。苏州科技大学音乐学院笛箫教授俞飞,在书香馨馨的“慢书房”给“青睐”游学团员们吹奏了江南笛箫的水乡韵调,与北笛的热烈不同,有种日落黄昏不如归去的牧笛带出幽幽乡愁的心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古琴专业的俞兰璟,玉手仙指弄琴弦,指尖上流淌出琴音若泉涌如涓的吟调,与教授老爸俞飞先生吹箫,即兴合奏,现代而又优雅盈盈,绕梁慢书房,诠释江南古典乐的独特美。
600年昆曲,500年评弹,皆出于苏州。昆曲的水磨调唱成了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评弹之吴侬软语则依旧淡然在水巷里咿呀着苏州的好风光。
文人是从园林里走出来的雅士,这就是昆曲研究专家苏州大学周秦教授。他讲起自小父辈言传身教的昆腔雅韵,讲起为白先勇先生《牡丹亭》青春版做顾问的艰辛历程,却完全是一种美的呈现。那讲述仿佛“笔墨秀”,悠悠绵绵,蚕丝般吐出如丝如缕的韵致,一派江南文人风骨。
在小桥观冷月碧落洒青石的月下,去黛瓦白墙的深处,走进斑驳映沧桑的丝丝苦涩中,听著名评弹师张凌平与唐蔚羽夫妇的吟诵,铿锵、哀婉、低叹、高唱以及承转启合的分寸韵味,将听众的情绪统统带入晚暮青烟缭绕淡淡的江南愁绪。
冬雨时节出行,最难捱愁。走过昆山千灯古镇,不去看桥上偶遇的撑伞人,那会让细雨流发朦胧了你的双眼。可去扣门,访顾炎武故居,与他聊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江山里的事儿。顾炎武讲天下而不言王朝,就是摒弃古代而强调古典之兴。然后去太仓,看刚发掘的元代瓷仓,龙泉瓷温润,发掘队长张志清老师的讲解,恍若他在天堂发现了古典美。
回到“慢书房”,书香、茶香、咖啡香,飘向被窗外浓雨打湿的文人情怀,与窗内的文泽笃厚共氤氲,畅谈苏州小巷里大历史的故事。多少惊喜,相视一笑?还有多少风流遗韵喋喋不休向我们走来,目不暇接中至今无法走出这古典主义美在泛滥的苏州。于京郊蝜蝂斋
2019年元月12日
绘图/朝阳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