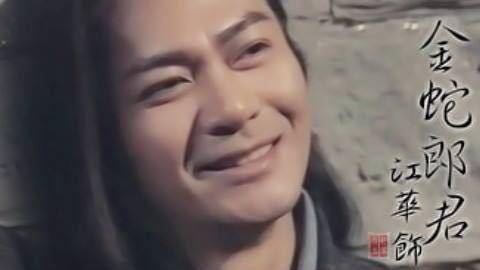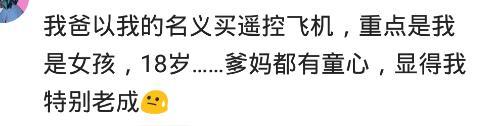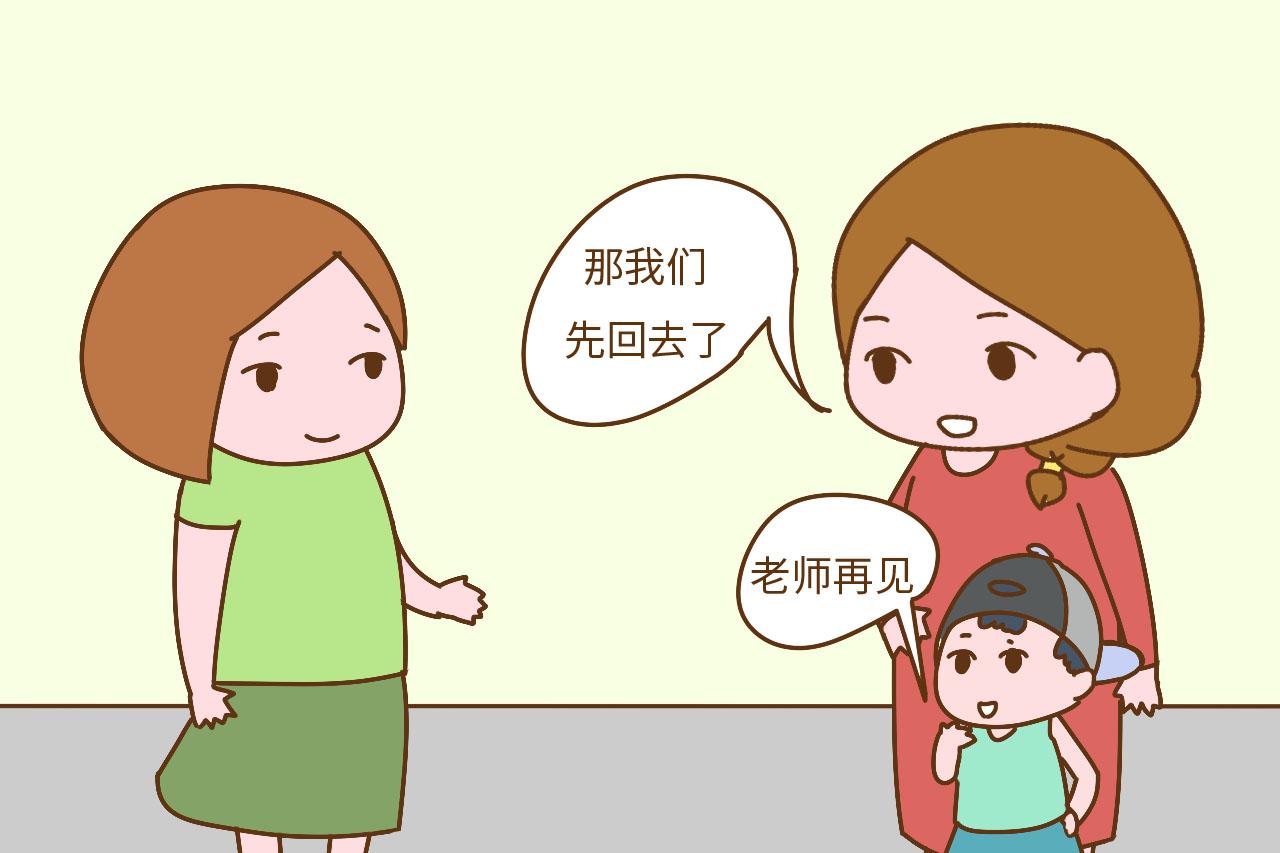黯然销魂臭鳜鱼
“你还记得在重庆吃铁匠火锅那次么?”
“光明桥那家特好吃的干锅鸭头,旁边卖鸡蛋灌饼的老奶奶有印象吗?”
“黄山吃臭鳜鱼那次,那小俩口还记得吗?”
是的,这是一条令人印象深刻的臭鳜鱼。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2004年黄山的屯溪老街,远没有现在热闹,店铺到了晚上10点基本就稀稀拉拉了。露天排挡倒是开始陆续冒了出来,都是躲避城管的营生。我们选的这家排挡刚开始营业,经营排挡的小夫妻,一边整理,一边吵架,男的基本不吭声,女的没一会便嚎啕大哭。哭着哭着抬头看到我们,马上擦干眼泪盈着笑脸招呼问吃点什么。这样苦的爱情,也是铁了心要过一辈子的。
应该没有受到情绪的影响,寡言少语的小伙做的那条1斤半的臭鳜鱼一点也不含糊。在十多年前,花68元点一份这样陌生的菜,有点孤注一掷,点盘最贵的菜,也是种态度。没想到臭鳜鱼原来是这般好吃,我们吃得很专注,就像人鱼小姐里马玛林说的:“两个人吃,死一个都不知道!”
女朋友跟老板娘说,你老公手艺真好,老板娘容光焕发,之前的大哭好像从未发生过。我问小哥,弄臭了还这么好吃是什么道理?小哥龇着牙笑着说:“堕落是为了飞翔。”
就这样,这条堕落并生成了很多记忆的臭鳜鱼,打开了我味觉的一个全新维度。

GIF来自网络
外地人到徽州,爬爬黄山,看看牌坊和祠堂,还得吃几个徽州菜,才算是不虚此行。时尚的酒楼,怀古的食肆,村边的小店,偷偷摸摸的排挡,都要将“臭鳜鱼”作为隆重推出的招牌菜。款款端上来时,总有食客会因其臭而掩鼻或皱眉,主人照例要说一段故事的。
都是些枝枝蔓蔓的花絮、轶闻,大众版本大抵如此:二百多年前,沿江贵池、铜陵一带的鱼贩子将鳜鱼运至徽州,途中为防止鲜鱼变质,商人将鳜鱼两面涂上盐巴,放在木桶中运输。抵达徽州之后,鱼已经发出了怪味,然而又舍不得丢掉,洗净热油细火烹调后,竟成了鲜香无比的佳肴并流传开来,成了一道“臭”名远扬的徽州名菜。
貌似一种民间粗鄙化饮食,却隐含着食不厌精的另一种高级形式。最初食臭鱼虽多是无奈之举,同时也是一种生活姿态:即便变质也不立即扔掉,想方设法地化腐朽为神奇探索出丰富的味道,还让包容与喜爱代代相传。
《太平广记》中详细记载着臭鱼的做法:当六月七月盛热之时,取鱼长二尺许,去鳞净洗。满腹内纳盐竟,即以末盐封周遍,厚数寸。经宿,乃以水净洗。日则曝,夜则收还。安平板上,又以板置石压之。明日又晒,夜还压。如此五六日乾,即纳乾瓷瓮,封口。经二十日出之……味美于石首含肚。
徽州臭鳜鱼的“酿造”与之相似:取一斤半左右的鲜鱼,净身抹精盐腌渍,一层一层码进木桶,压上青石或鹅卵石,在25℃左右的室内并通风的环境中腌渍4天,夏天腌渍两三天,冬天腌渍七八天。还要每天上下翻动鱼身,确保腌渍均匀。时间无法标准化,要根据鱼的大小、气温变化来决定时间。这个道理并不复杂,好比你每天和我吃同样多的食物,走同样多的步数,照样长不出我同样多的肉。
很多时候,香和臭只有一线之隔。很多臭味在稀释很多倍之后,产生的就是香味。

GIF来自网络
有些香气浓度超高后,气味会比一般的臭气还难闻,比如狭小的电梯里遇到喷了很多香水的女子。
臭鳜鱼并非以追求臭为己任,在腌制过程中经过石头压住,充分发酵的同时,腥味随着水分渗出,鲜味的集中度更高,鱼肉更加紧实弹韧。
和臭豆腐相比,虽然所产生臭味的物质不同,但原理是一样的:发酵过程中,食物中的蛋白质被微生物分解,产生有鲜味的氨基酸,比如谷氨酸,正是它们使食物变得鲜美可口。而在乳酸菌、葡萄球菌和酵母菌的作用下,鱼肉也变得更加鲜嫩爽滑。而产生臭味的物质,多以挥发性气体存在,在烹饪的过程中,大部分的臭味物质可能都挥发掉了,“闻着臭,吃着香”,由此而来。
好吃的臭鳜鱼,取料鲜活是第一要义,同时,春天的鳜鱼为佳。
“桃花流水鳜鱼肥”,徽州山区桃花盛开时,雨水连绵,溪水上涨,鳜鱼跃出石隙,活跃在水草丰茂的浅水中追食丰盛的鱼虾,此时鳜鱼比其它鱼类更为肥美。它的食性有点像豹子,靠伪装和速度冲出去捕食,极强的爆发力锻炼了它不失韧性的肌肉。经过一个春天的“大吃大喝”,体内积蓄的营养开始向性腺转移,繁殖季节开始,肉质便不如清明前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