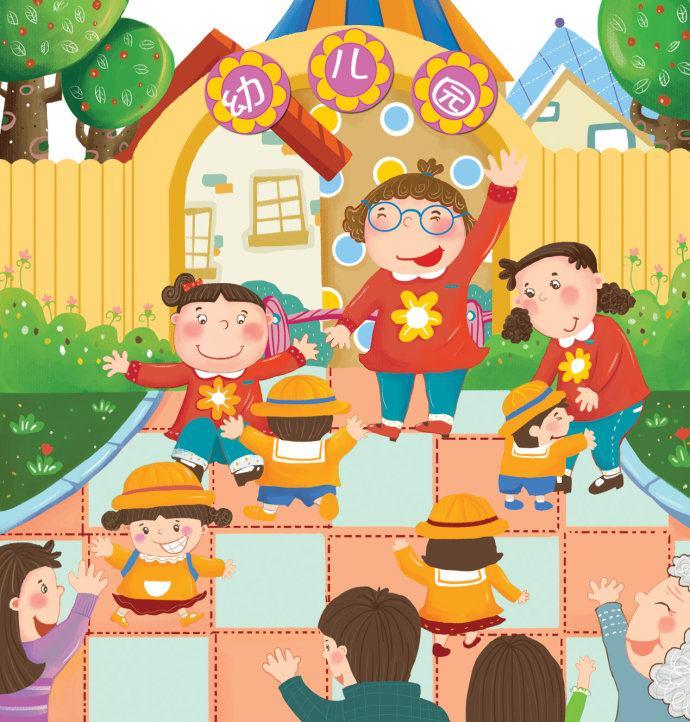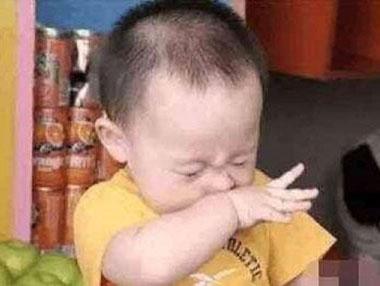玛丽娜莉:一位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人们常说,历史是一位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果真如此的话,她的名字可能叫玛丽娜莉。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印第安女性数百年来形象虚实难辨,声名毁誉各半:她是一位公主、语言大师、女英雄,还是一个女奴、妓女、叛国者?用这位纳瓦族女性的丰茂发辫,后世不断编织着征服者的凶残与狡黠,以及被征服者的屈辱与迎合,书写出一部殖民史、女性史、语言史——或许,用福柯的话来说,还是一部权力史、一部性史。
玛丽娜莉的传奇人生
玛丽娜莉的故事发生在五百多年前西班牙人征服美洲的时代。众所周知,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美洲有发达的本土文明。在中美洲地区,有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在今秘鲁和南美西部沿海狭长地带,有印加文明。1492年,热那亚人哥伦布受西班牙王室的资助,首航到达美洲,“发现了新大陆”。由此,美洲本土文明开始与外来的欧洲文明碰撞与融合。
在阿兹特克文明中,有一支纳瓦族人,主要活动在今天墨西哥中部一带。我们故事的主角就出生于一位纳瓦族首领的家庭,算得上出身高贵。她降生的日子,恰逢纳瓦族的一个重要节日——绿草节,因此父母给她取名“玛丽娜莉”(Malinalli),意思是“草地女神”。她可能出生于1496年,另说1501年。这时候,西班牙征服者已经在古巴群岛建立了定居点,打算渡过尤卡坦海峡,进入纳瓦族人居住的墨西哥一带。
玛丽娜莉与众多红颜薄命的故事主角一样,命途多舛。在她年幼的时候,父亲过早地去世。母亲改嫁给另一个部落的首领,于是玛丽娜莉有了一个异父的弟弟。母亲为了保全儿子和她自己的地位,偷偷将玛丽娜莉送给或者说卖给了别人,并对外宣称女儿已经死了。
此后,这位大家闺秀沦为女奴,在玛雅文明区域几经易手,身世飘零。玛丽娜莉先是被卖给希泊巴的一位地产主。希泊巴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国家,今天已湮没在历史中,人们从今天著名的同名墨西哥重金属乐队身上,可以想象它昔日的辉煌。后来她又被卖给玛雅城市波多卡的酋长,这里是今天盛产辣椒的塔巴斯科的前身。
1519年,西班牙人赫尔南·寇蒂斯(Hernán Cortés, 1485-1540)率远征军从伊斯帕尼奥拉岛(今属古巴)向墨西哥地区进发。很快,寇蒂斯的军队征服了波多卡。酋长挑选了20位女奴,献给征服者,为他们做饭,玛丽娜莉是其中之一。西班牙人不愿意吃非基督徒做的食物,他们使女奴们受洗,接受基督教信仰,玛丽娜莉有了受洗名——“玛丽娜”(Marina)。或许是机缘巧合,纳瓦语中的“玛丽娜莉”与西班牙语中的“玛丽娜”十分接近,这似乎为这位奇女子的命运添加了令人遐思的注脚。

玛丽娜莉等20个女奴被送给寇蒂斯,版画,现藏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班克罗夫特图书馆。
豆蔻年华的玛丽娜莉堪称绝世佳人。寇蒂斯的远征军中有一位叫迪亚士的士兵记述了玛丽娜莉的美貌与优雅,说“她是唯一一位让我记住名字的奴隶”,只不过,他记住的名字应该是“玛丽娜”。寇蒂斯将美丽的玛丽娜莉从众多女奴中挑选出来,送给另一名部下、征服者中唯一出身贵族的西班牙人阿朗索。后来,寇蒂斯派遣阿朗索回西班牙,向国王查理五世报告新世界已被征服。
阿朗索离开后,寇蒂斯又将玛丽娜莉召回身边,因为寇蒂斯发现玛丽娜莉不仅美丽动人,而且天资聪慧,具有过人的语言天赋。玛丽娜莉在阿兹特克与玛雅两个地区都生活过,会讲阿兹特克的纳瓦语,也会讲玛雅语。她还从阿朗索那学会了一些基本的西班牙语。当时,阿兹特克地区有一个操纳瓦语的使团来到波多卡,但与西班牙人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语言。有一位西班牙神父阿圭勒曾被玛雅人俘获,在玛雅人中生活多年,学会了一些玛雅语。这样,在玛丽娜莉与阿圭勒的协作下,使团与西班牙人得以沟通。
玛丽娜莉不仅具有美貌和语言天赋,还深谙阿兹特克及玛雅各部族之间的交往规则,也懂得部族军事冲突中惯用的战术。寇蒂斯对玛丽娜莉加倍器重。位于今天墨西哥中部的乔卢拉部族以建造金字塔而为后世所知。当时,这个部族曾与阿兹特克人联合,打击一小股西班牙军队。玛丽娜莉向寇蒂斯通风报信,寇蒂斯成功地避开了乔卢拉人布下的陷阱,并施行报复性屠杀。
特诺奇蒂特兰城是阿兹特克人的中心城市,1521年底,西班牙人攻陷该城,后在其基础上建成今天的墨西哥城。在特诺奇蒂特兰城以南大约八公里,有个小镇名叫约阿坎,今天已是大墨西哥城的一个城区。寇蒂斯在约阿坎镇为玛丽娜莉盖了一间房子。1522年,玛丽娜莉产下一子,寇蒂斯赐其父姓,取名马丁·寇蒂斯(Martín Cortés)。1524年,洪都拉斯人发起反叛,寇蒂斯带着玛丽娜莉一同前往镇压。
今天墨西哥中部的奥里萨巴镇以火山风景知名,当时是阿兹特克人的一个要塞。在这座小镇,在寇蒂斯的授意下,玛丽娜莉与西班牙贵族胡安·哈拉米约(Juan Jaramillo)结婚,育有一女,取名玛丽亚。
此后,玛丽娜莉的人生轨迹失去了历史线索。历史学家判断,她可能死于1551年。她的儿子马丁早先在寇蒂斯的家庭里被抚养,后来,寇蒂斯成功地向西班牙当局申请,使马丁的身份合法化。马丁回到西班牙,穿上戎装,成为王室的一名骑士,获得唐马丁(Don Martín)的尊称。女儿玛丽亚后来也随生父胡安回到西班牙,胡安后来续弦,与第二任妻子一起抚养玛丽亚长大成人。
形象变幻不定的玛丽娜莉
历史人类学家发现,在非洲的斯瓦希里语部族中,人被分为三类:活人、“撒哈”(sasha)和“扎马尼”(zamani)。如果去世的人与还活在世上的人曾活在某个共同的时间段,这种人就是“撒哈”,即活的死人。他们还没有完全死去,因为他们还能出现在某个活着的人的记忆中,活着的人可以通过思想回忆他们,通过艺术重塑他们的样子,通过故事使他们再生。当最后一个认识先人的人死去后,那个先人就不再是“撒哈”,而成为“扎马尼”,即死人。如果是大众化的先人,“扎马尼”非但不会被遗忘,反而会得到尊敬。
借用这套民俗话语,我们发现,玛丽娜莉的传奇也有着相应的不同版本,这首先表现在她的众多称谓上。“玛丽娜莉”是其闺名;“玛丽娜”是其天主教受洗名,后世西班牙人尊称其为“唐娜玛丽娜”(Dona Marina);墨西哥人称其为“拉玛琳卡”(La Malinche);在一些亲西班牙人的土著人嘴里,玛丽娜莉与寇蒂斯共用一个名字——“玛琳斯”(Malintzin);此外还有一些代称。如此众多的称谓反映了我们这位传主不同的人类学面向。为方便叙述,本文在大多数语境中采用其出生名。
玛丽娜莉大约活了30多岁,她在世的时候,关于她的传奇故事就到处流传。在她所生活的阿兹特克与玛雅文明区域,在欧洲人到来之际,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文字系统,玛丽娜莉的故事主要靠口口相传,存世的主要是一些绘画作品,以及西班牙征服者的记录。西班牙人德沙哈衮修士关于美洲风物的记录现藏于佛罗伦萨的图书馆,被称为《佛罗伦萨抄本》(Florentine Codex, 1569),这部经典文献中不乏涉及玛丽娜莉的信息。在很多阿兹特克的绘画中,玛丽娜莉与寇蒂斯的形象经常相伴出现。“玛琳卡”出现在很多壁画里,有时与寇蒂斯在一起,很多时候是独自一人在指挥作战。

玛丽娜莉为使团做翻译(出自《佛罗伦萨抄本》(Florentine Codex, Book 12)。
在玛丽娜莉去世后的很长时间里,不管是西班牙人的史书中,还是本土的原始记事中,很少有对其大加鞭挞。实际上,只是到了1810年墨西哥革命成功后,玛丽娜莉才受到谴责,“玛琳卡”这个名字成为叛徒的代名词。共和国痛恨一切与西班牙有关的事物,玛丽娜莉因为与寇蒂斯有染,自然遭到仇恨,甚至是更严重的仇恨。玛琳卡被当作一个符号,形容那些帮助西班牙征服者破坏本土美洲人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与文化,盘剥美洲人民的人。由此,出现了一个词“玛琳卡主义”(malinchismo),表示背弃自己的本土身份,迷恋外来事物。玛丽娜莉也不再是为这片无知的土地带来基督光明与解放的“伟大的征服者”,而变成了“寇蒂斯的情妇”,靠出卖肉体达到自己的目的。男人们诅咒她,担心自己的妻子或女儿会群起效仿,危及男性主导的社会传统。
现代讲述者对玛丽娜莉念念不忘、津津乐道,以她为主题的小说、戏剧、音乐、绘画层出不穷。在这些形式多样的作品中,玛丽娜莉的形象变幻不定。玛丽娜莉的传奇身世,更是为拉美文学标志性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注入了不竭的灵感。
1893年,《所罗门王的宝藏》作者、英国著名小说家亨利·R.哈格德爵士发表小说《蒙特祖玛皇帝的女儿》(中译本林明榕、易敏译,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认为玛丽娜莉是阿兹特克一世皇帝蒙特祖玛的女儿。小说以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为背景,描述了玛丽娜莉的传奇人生。
1939年,匈牙利作家拉斯洛·保舒特出版小说《雨神为墨西哥哭泣》,饱受赞誉,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这部小说中,玛丽娜莉是一位基督徒、同胞的保护者。
1955年,墨西哥著名小说家胡安·鲁尔福出版小说《佩德罗?巴拉摩》(中译本屠孟超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这部小说以佩德罗?巴拉摩这位西班牙入侵者的恶行作为远景,叙述了毁灭时代里玛丽娜莉所代表的母性悲情,台湾大学张淑英教授认为,这是一部“生枯起朽的魔幻”。
1963年,美国多产作家艾迪森·T.马歇尔将自己的小说直接取名为《寇蒂斯与玛丽娜》,在他的叙述中,玛丽娜莉变成了玛丽娜,是寇蒂斯的情人、翻译和参谋。
墨西哥著名诗人、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在其长篇散文《孤独的迷官》(1950)中,将拉玛丽娜莉塑造为墨西哥文化的母亲。这篇散文共九章,其中第四、五章的标题分别为“拉玛琳卡的儿子们”和“征服与殖民主义”。帕斯的祖父是西班牙人,祖母是印第安人。他早年受的是欧式教育,对文化融合给墨西哥人民及西班牙人带来的困扰有深刻感受。帕斯继承了聂鲁达的风格,扎根于印第安文化,巧妙地融合了东西方文化。他还翻译过王维、李白等中国古典诗人的诗歌。
汉斯·拜姆勒与罗伯特·H. 沃尔夫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合作创作的小说和电影《星际迷航》中,太空舰的名字就叫“玛琳卡”。汉斯·拜姆勒是土生土长的墨西哥人,父亲曾是德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二人后来继续合作,以玛丽娜莉为素材,借用伊索寓言的典故,写作了电影剧本《鹰与蛇》(2009年上映)。
玛丽娜莉还被赋予了女性主义的角色,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今天,英语中有一个单词chicana,专指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女人,即“奇卡娜”(男性叫“奇卡诺”,chicano)。在民权运动中,“奇卡娜”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她们在为平等权利斗争时,经常以“玛琳卡”为榜样。很多拉丁女性主义者反对先前视玛丽娜莉为替罪羊的做法。在现代,在很多风俗画中,玛丽娜莉经常与圣母玛丽、拉里奥罗娜以及拉索达德拉(La Soldadera,在墨西哥革命期间与男人并肩作战的妇女)等英雄角色相提并论。墨西哥女性主义者为玛丽娜莉辩护,认为她是一个处在不同文化夹缝里的妇女,不得不做出复杂的决定,说到底,她是一个母亲,一个新族群的母亲。

寇蒂斯、玛丽娜莉及儿子,青铜群雕,位于墨西哥城梅斯蒂索人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