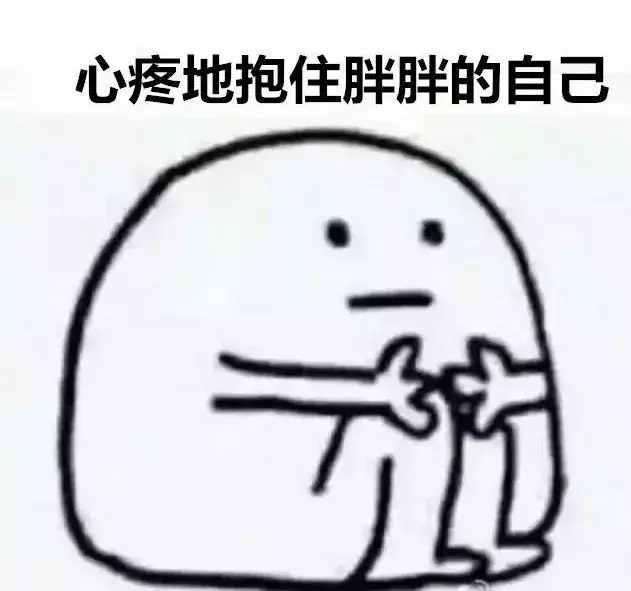清代学术风尚表现,政治到文化的过渡时期
导语:清代学术风尚表现,政治到文化的过渡时期
清代学术风尚总体表现为以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整理与总结为大端。如果说清初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所崇尚的经史之学是一种倡导与推动的话,那么,清中期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考据学既是对清初以来愈加明显的朴学风尚的一种升华与完善,更是开启一代学术新风的典型。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基本学术规范的汉学传统,在清代学人特别是清中期学人中深入人心,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艺术探索,均有浓厚的追源溯流的情结。

清代朴学的盛行,显然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的泛滥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清初学者尚有明季学术风气的话,那么,主客观因素已经导致乾、嘉诸老的学术与前辈经世致用之学迥然有别了。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明清之际,诸家治学,尚多东林遗绪。梨洲(黄宗羲)嗣轨阳明(王守仁),船山(王夫之)接迹横渠(张载),亭林(顾炎武)于心性不喜深谈,习斋(颜元)则兼斥宋明,然皆有闻于宋明之绪论者也。

不忘种姓,有志经世,皆确乎成其为故国之遗老,与乾嘉之学,精气夐绝焉。”又说:“今(乾隆帝)曰‘以天下治乱为己任尤大不可’,无怪乾嘉学术一趋训诂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囿矣。于此而趋风气,趁时局,则治汉学者必以诋宋学为门面,而戴东原(震)氏为其魁杰。起而纠谬绳偏,则有章实斋(学诚),顾曰:‘六经皆史,皆先王之政典。’然为君者既不许其以天下治乱为己任,充实斋论学之所至,亦适至于游幕教读而止,乌足以上媲王介甫(安石)、程叔子(颐)之万一耶!”“文字狱”政策就是当时社会的客观因素,而一代学者的学风转型则是主观因素。前者是“被动”因素,后者则是“主动”因素。两者的关系是“主动”在“被动”地得到政策的“支持”与“理解”,并为之提供最好的学术条件。

在乾隆、嘉庆两朝,朴学大兴,形成了以经史考证为核心的学术主流,从而形成与历史上的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可相并列的“乾嘉学派”考据学。乾嘉朴学又称“汉学”、“考据学”,自乾隆朝初叶即登上历史舞台,风光一直延续到道光朝中期,百余年间人物彪炳,成果千秋,最为大观。乾嘉学派折入追究名物训诂之途的考据作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传统学术“经世致用”的主旨,但继承和发扬了东汉许慎的古文经学,以求回归儒家原典寻根找源的实证学风,又成为一种学术典范,对此后的中国传统学术起到了历久不绝的影响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朝统治者很好地利用了汉族(特别是中原和江南)士人中自晚明以来就已经颇具影响的针对宋明理学所作的反思,将一代颇有声望的学者引导到了远离“经世致用”传统经史之学的学术轨道上,实现了从政治到文化的顺利过度。因此,清代满族统治者就实际上是有效利用了高度成熟的汉族文化,从而实现了政权的稳定,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被同化”。

针对受“欧美风雨”学风熏染的民国学者所提出的满清入关后最终为汉族文化所同化的流行观点,钱穆是非常不予认同的:“满清最狡,入室操戈,深知中华学术深浅而自以利害为之择,从我者昌尊,逆我者贱,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中,其为人高下深浅不一,而皆足以坏学术、毁风俗而贱人才。故以玄烨(康熙)、胤禛(雍正)、弘历(乾隆)踞其上,则幸而差安,以顒琰(嘉庆)、旻宁(道光)、奕詝(咸丰)、载淳(同治)、载湉(光绪)、载淤为之主,则终不免于大乱。而说者犹谓满族入关,卒为我所同化,政权推移,中华之文运依然,诚浅之乎其为论也。”

诚如学者所谓:“学术变而考古,学士通人心究篆隶。一代之文艺,固由一代之功令推激而成,书道所系亦重矣。”与清代学术思潮的变迁相呼应,书法艺术虽然保持了它的民族文化纯粹性,但也经历了明末清初学人导夫先路,道、咸时期实现碑学洪流对传统帖学的大冲击,这样一个中国书法史上从技法到流派的最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