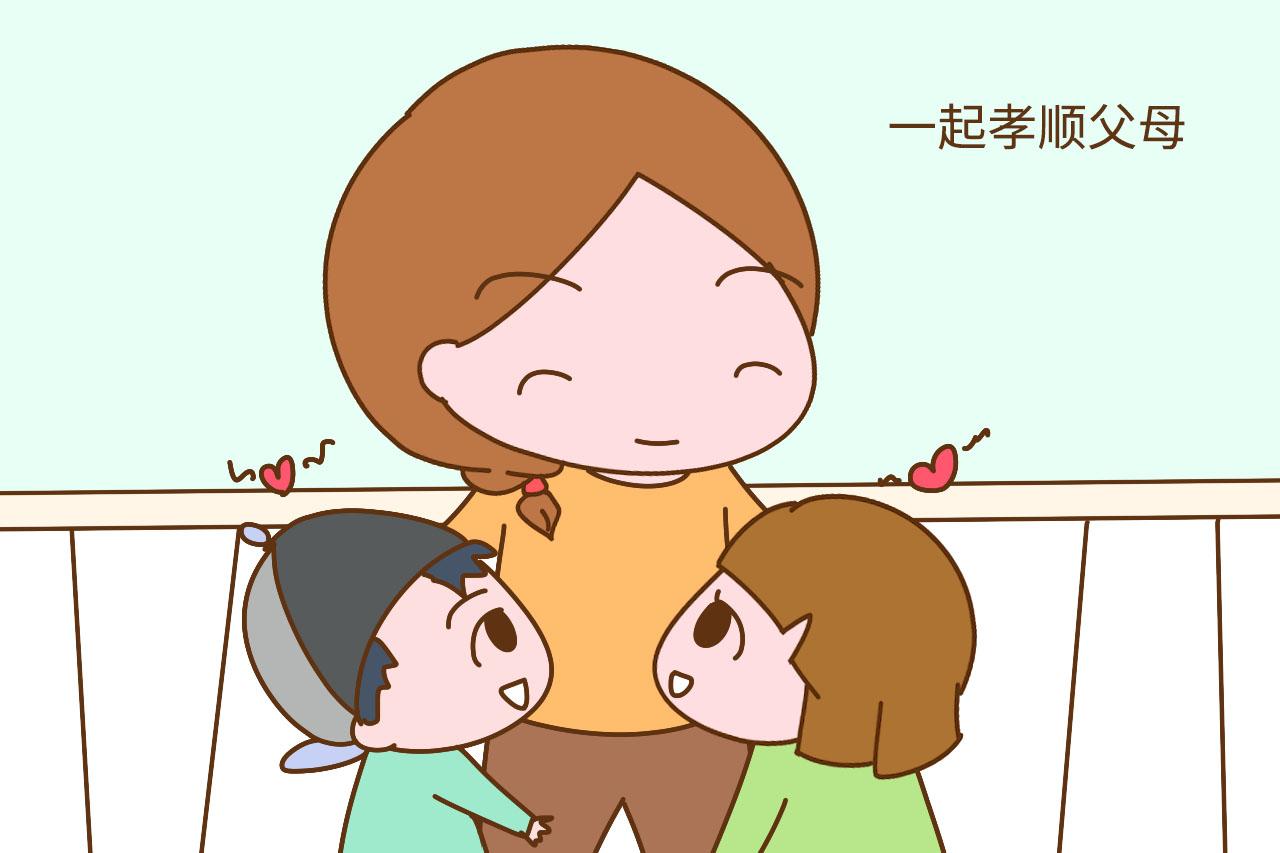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
2018年10月30日,94岁的查良镛与世长辞。63年前,他首次以“金庸”为笔名拟写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1959年他在香港创办《明报》,并在自办的《明报》上连载《神雕侠侣》。
陈平原教授曾在书中写到,金庸“下午褒贬现实政治,晚上揄扬千古侠风。有商业上的野心,但更有政治上的抱负”,“正是政论家的见识、史学家的学养,以及小说家的想象力,三者合一,方才造就了金庸的辉煌。”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今天分享陈平原教授《千古文人侠客梦》中的一篇文章,以此长久缅怀一生“笑傲江湖”的金庸先生。
千古文人侠客梦

文 | 陈平原
原文标题: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
1.
作为本世纪最为成功的武侠小说家,金庸从不为武侠小说“吆喝”,这点值得注意。在许多公开场合,金庸甚至“自贬身价”,称“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如此低调的自我陈述,恰好与在场众武侠迷之“慷慨激昂”形成鲜明的对照。将其归结为兵家之欲擒故纵,或者个人品德之谦虚谨慎,似乎都不得要领。
在几则流传甚广的访谈录(如《长风万里撼江湖》、《金庸访问记》、《文人论武》、《掩映多姿跌宕风流的金庸世界》)中,金庸对于武侠小说的基本看法是:第一,武侠小说是一种娱乐性读物,迄今为止没有什么重大价值的作品出现;第二,类型的高低与作品的好坏没有必然联系,武侠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有好也有坏;第三,若是有几个大才子出来,将本来很粗糙的形式打磨加工,武侠小说的地位也可以迅速提高;第四,作为个体的武侠小说家,“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如此立说,进退有据,不卑不亢,能为各方人士所接受,可也并非纯粹的外交辞令,其中确实包含着金庸对武侠小说的定位。
可是,请别忘了,撰写“娱乐性读物”的,只是文化人查良镛的一只手;还有另外一只手,正在撰写“铁肩担道义”的政论文章。据我猜想,在很长时间里,查氏本人更看重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据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这话用在查氏创业之初,当不无道理。为了吸引广大读者,查良镛以《神雕侠侣》等作为诱饵——如此陈述,很容易消解小说家金庸的“意义”。但我宁愿相信,这是实情。因为,在我眼中,查先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也正是这一点,使其在本世纪无数武侠小说家中显得卓尔不群。
五四以降,创作态度稍为认真的武侠小说家,面对新文学家义正词严的道德讨伐,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敢于理直气壮地为自家创作辩护的,寥寥无几,而且也都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原因是,著名的新文学家多为“大知识分子”,政治上举足轻重,在文坛上更是能够呼风唤雨,其社会地位及影响力,绝非卖文为生的平江不肖生们可比。另外,新文学家之批评“旧派小说”的“金钱主义”以及以“消闲”为唯一旨趣,基本上击中要害。在本世纪末以前的中国,文人无论新旧,对于纯粹“游戏”、“消闲”的作品,评价历来不高。一句“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便足以使金庸放弃为武侠小说辩护的责任。至于金庸本人,为何一面自贬身价,一面乐此不疲,因其另有崇高志向——具体说来,便是《明报》的事业。
有了《明报》的事业,金庸与无数武侠小说家拉开了距离。一个武侠小说家,不只是娱乐大众,而且可以引导社会舆论,在金庸奇迹出现以前,实在不能想象。据说,金庸撰写的社评与政论,总共约两万篇。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
查氏之政论文章,读者面自然远不及其武侠小说,可备受学者及政治家的关注。前者以金耀基为例:在率领香港中文大学诸学者“文人论武”时,金氏大谈对于查先生所撰社论之热爱,称其“知识丰富,见解卓越,同时有战略,有战术,时常有先见之明,玄机甚高,表现出锐利的新闻眼”。
作为小说家的金庸早已金盆洗手,而作为政论家的查良镛仍然宝刀不老,表面上二者有时间差,可这不妨碍我们将其相提并论。因为,在金庸创作的高峰期,左手政论,右手小说。我关注的是,这种写作策略,使武侠小说家金庸一改“边缘”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介入了现实政治与思想文化进程。
既不完全认同新文学家的“雅”,也不真正根基于武侠小说家的“俗”,而是两面开弓,左右逢源。支撑起如此独立不羁的言说的,乃是其作为“舆论家”的自我定位以及由此而派生的“道义感”。晚清以降,文学的雅俗之争,有审美趣味的区别,但更直接的,还是在于社会承担:一主干预社会,一主娱乐人生。查氏起步之处在新闻,现代中国的新闻事业,恰好与武侠小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绝大部分武侠小说,都是先在报刊连载,而后才单独刊行的)。可是,同在一张报纸,头版的社论与末版的副刊,各有各的功能,几“不可同日而语”。金庸自办报纸,并且“赤膊上阵”,下午褒贬现实政治,晚上揄扬千古侠风。有商业上的野心,但更有政治上的抱负。长期坚持亲自撰写社评,实际上认同的是新文化人的担当精神——这才能理解金庸为何对作为一种“娱乐性读物”的武侠小说评价并不高。
金庸曾表示,当初撰写武侠小说,固然有自娱的成分,主要还是为了报纸的生存。如此“动机不纯”,难怪其对于仅局限于此的同道,不太恭维。时至今日,金庸仍是第一个在小说之外还有显赫功绩的武侠小说家。查氏本人对此十分自豪。在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仪式上,出现一个有趣的局面:校方表彰的是“新闻学家”,金庸演讲的是“中国历史”。至于武侠小说,依然“不登大雅之堂”。“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如此立说,确实让无数“金迷”大失所望。不愿意只是被定义为“武侠小说家”,金庸于是不时提醒读者,请关注他真正的“学问”。
其实,关于金庸的传记或著述,大都会提及其值得夸耀的“《明报》的事业”。本文只是将常见的“并列句”改为“因果句”,而且不是从《神雕侠侣》对于《明报》销量的决定性影响立论,而是反过来,强调办报纸、写社评对于《笑傲江湖》等小说创作的意义。社论与小说,一诉诸理性与分析,一依赖情感与想象,前者需要“现实”,后者不妨“浪漫”。如此冷热交替,再清醒的头脑,也难保永远不“串行”。只要对当代中国政治略有了解,都会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中读出强烈的“寓言”意味;可金庸本人偏偏极力否认其有所影射。在《笑傲江湖》的《后记》中,金庸称:
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划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
其实,小说家之追求普遍意义,与政论家的注重现实感慨,并不完全抵牾。说“影射”或许过于坐实,但对“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极度反感,毕竟包含着明显的现实刺激。
即便小说家无意影射,政论家的思路也不可能严守边界,不越雷池半步。就在左右手交错使用之际,不可避免地,“串行”发生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无影射,二说皆可。就像六朝人娴熟藻绘骈偶,即便无意为文的著述,在后人眼中,也都颇有“文章”的韵味。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入世精神;即便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理解查君的这一立场,不难明白其何以能够“超越雅俗”。儒道之互补、出入之调和、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大侠精神之阐发,也体现为小说与政论之间的巨大张力。

2018年10月31日,《明报》头版“大侠笑别,江湖传世”
2.
武侠小说与《明报》社评,二者不可通约,可也并非完全绝缘。强调金庸的小说与政论之间的互补关系,其实是为了指向武侠小说之特色:极大的兼容性。很难想象言情小说或侦探小说也能如此“兼容”政治与社会、文化与历史。篇幅巨大,有足够的空间可供小说家纵横驰骋,这并非主要原因。关键在于,作为一种小说类型,武侠小说从一诞生起,便趋向于“综合”。
同是武侠小说家的古龙,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在一次与金庸的座谈时,曾称:
武侠小说有一点不易为人公认,甚至武侠小说的作者也鲜少意识到的,那就是武侠小说可以融合各种小说类型及小说写作技巧。
古龙举出金庸的小说对于历史小说、推理小说和爱情小说的借鉴。其实,这并非金庸个人的独创,而是小说类型的内驱力决定的。
在我的论述框架中,游侠文学源远流长,但作为小说类型的武侠小说,则只能说是后起之秀。清代侠义小说在其走出混沌状态的过程中,从公案小说学来长篇小说的结构技巧,从英雄传奇学来打斗场面以及侠义主题,又从其对手风月传奇那里学来了“既侠又情”。进入二十世纪,武侠小说的声威日渐壮大,其综合能力也日渐高超,以至逐渐成了章回小说的代表。六十年代范烟桥改订《民国旧派小说史》时,论述的次序是言情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九十年代王先霈等主编《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武侠小说已经成了通俗文学的排头兵,而后才是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等。后起的武侠小说,有能力博采众长,将言情、社会、历史、侦探等纳入其间,这一点,其他小说类型均望尘莫及。这就难怪,世人之谈论“仍然健在”的传统中国小说,很容易举出武侠小说作为代表。
武侠小说之日渐走向综合,必定对作家的学识与修养提出较高的要求。可以像古龙那样凭借个人天赋出奇制胜,但武侠小说的“名门正派”,非金庸莫属。《碧血剑》之附人物论《袁崇焕》、《射雕英雄传》书后之成吉思汗家族诸传记、《倚天屠龙记》之描写明教及元末历史、还有《鹿鼎记》中大量的注解,都只是金庸学识的冰山一角。凡读过金庸小说的,无不对其历史知识与文化修养之丰厚留下深刻印象。这里举两篇文章为例。
游侠精神之值得关注,与武侠小说的发展前景,二者并不完全等同。金庸的成功,既是武侠小说的光荣,也给后来者提出巨大的挑战:武侠小说能否再往前走?文学史家及金庸本人均承诺,大作家的出现,可以提升一个文学类型的品位。这自然没错,可还必须添上一句:能否继续发展,取决于文类的潜力及预留空间的大小。从《三侠五义》到《笑傲江湖》,一百多年间,武侠小说迅速走向成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接下来的话,可就令人泄气了:“惟后来仅有拟作及续书,且多溢恶,而此道又衰落。”金庸等人的崛起,又使得此“宋人话本正脉”再度接续,且大有发展余地。鲁迅所说的“平民文学”,包括精神和文体。前者定位在庙堂之外,自是十分在理;后者局限于“话本正脉”,则略嫌狭隘。
或许,下个世纪武侠小说的出路,取决于“新文学家”的介入(取其创作态度的认真与标新立异的主动),以及传统游侠诗文境界的吸取(注重精神与气质,而不只是打斗厮杀)。某种意义上,金庸已经这么做了;但我以为,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些。毕竟,对于史家与文人来说,游侠精神,是个极具挑战性且充满诱惑力的“永恒的话题”。
1998年5月13日于京北西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