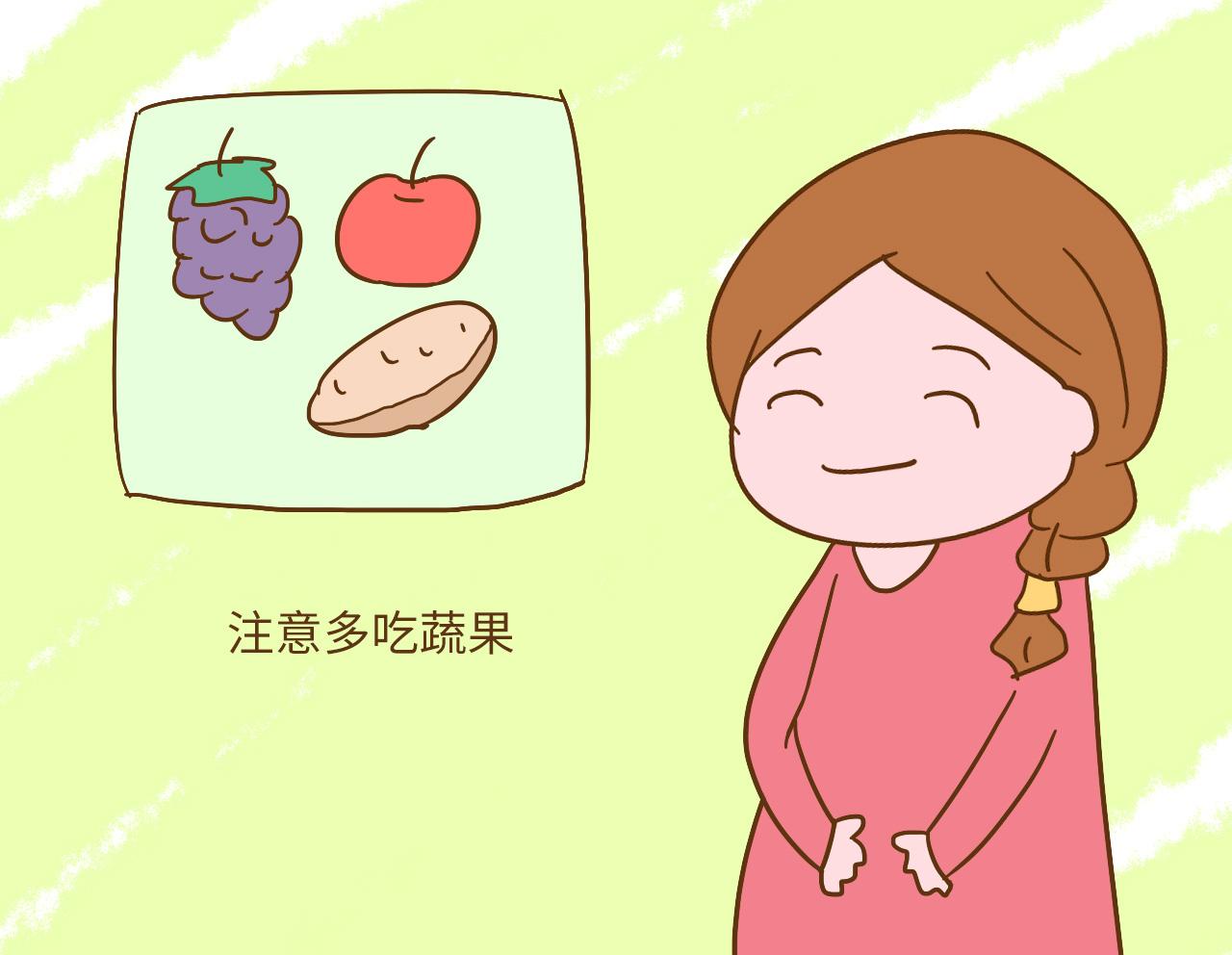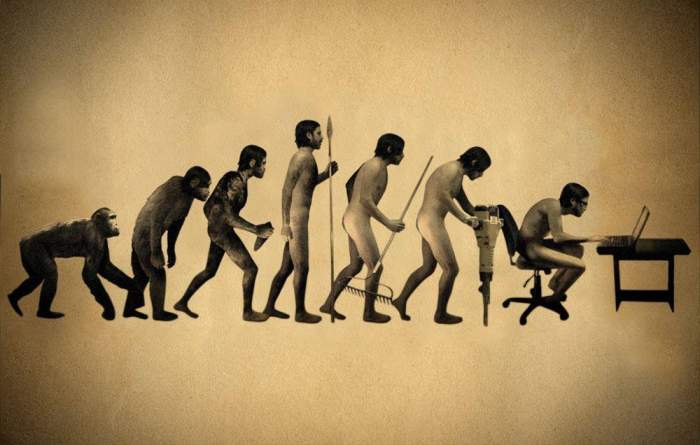海德格尔:泰然任之

孔拉丁·克洛伊采(Conradin Kreutzer,1780-1849年):德国著名音乐家和作曲家,出生于梅斯基尔希。为早期浪漫派代表人物之一。本文为海德格尔在家乡梅斯基尔希举行的孔拉丁·克洛伊采诞辰一百七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庆祝会成员!亲爱的乡亲们!我们聚集一堂纪念我们的同乡,作曲家孔拉丁·克洛伊采。
但是,庆典因此就已经是一个纪念庆典吗?我们思想,这当然是一个纪念庆典不可缺少的。只是,我们应该在纪念一位作曲家的庆典中思想什么并且说什么呢?音乐已经通过它的声音的乐声来“说话”,从而不需要普通语言,即言辞的语言——这难道不正标志着音乐的特性吗?人们是这样说的。不过仍然有问题:用演奏和歌唱来庆祝就已经是纪念庆典——我们在其中思想的一个庆典了吗?恐怕并非如此。所以,主办人在节目中加上一个“纪念讲话”。它应该帮助我们达到对所庆祝的作曲家及其作品的思念。一旦我们重新描绘孔拉丁·克洛伊采的生活历史,一一列举并描述他的作品,则这样的思念就成为富有生命的。我们能够通过这样一种叙述体会到某种欣悦和沉痛,体会到富有教益的和具典范性的东西。当然,归根到底我们只是通过这样一种讲话而让自己过得愉快。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在倾听这样的叙述时思想,也即思索某种在其本质上直接地且持久地触动我们每个个人的东西。因此之故,甚至一个纪念讲话依然还没有作出保证,保证我们在纪念庆典中思想。
我们不要给自己做任何姿态。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似乎由于职业而思想的人,我们大家往往是够思想贫乏的了;我们所有人都是太容易无思想的了。无思状态是一位不速之客,它在当今世界上到处进进出出。如今人们把一切的一切以最快速和最廉价的途径纳入知识,又同样迅速地忘却于同一瞬息。如此这般地一个聚会追逐着另一个聚会。纪念庆典变得越来越思想贫乏。纪念庆典和无思状态一起和睦相处。
然而,在我们是无思想的同时,我们却并没有放弃思想的能力。我们甚至急需这种能力,当然是用一种奇特的方式,亦即我们于无思状态中闲置我们的思想能力。可是能够闲置的只是这样的东西,它于自身中是生长的根基,比如一块耕地。上面什么也不长的高速公路也从来不会是一块耕地。正如只因为我们是听者,所以才会聋,正如因为我们曾年轻,所以才会老,同样地,我们之所以也会变得思想贫乏甚至无思想,是因为人在其本质之基础上具有思想的能力,具有“精神和理智”,并且是被注定要去思想的。只有这个我们在知或不知之中所拥有的东西,也才是我们能够失去或者——正如人们所谓——丢掉的东西。

▲ 海德格尔在黑森林
可见,增长着的无思状态乃基于一个消耗着当今人类的至内精髓的过程,即:当今人类在逃避思想。这种对思想的逃避是思想之失去的原因。属于这种对思想的逃避的还有:人既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承认其对思想的逃避。今日人类甚至断然否认这种逃避。他认为情形与此相反。他要说,也有充分的理由说: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做如此广泛的规划,如此众多的调查,如此狂热的研究。确实如此。这种洞察力和思考的奢意耗费有其巨大的效用。这样的思想仍不可缺少。然而——尽管如此,它只不过是一种特殊方式的思想。
它的特性在于:当我们进行规划、研究和建设一家工厂时,我们始终是在计算已给定的情况。为了特定的目标,出于精打细算,我们来考虑这些情况。我们预先就估算到一定的成果。这种计算是所有计划和研究思维的特征。这种思维即使不用数来运行,不启用计数器和大型计算设备,也仍然是一种计算。计算性思维权衡利弊。它权衡进一步的新的可能性,权衡前途更为远大而同时更为廉价的多种可能性。计算性思维唆使人不停地投机。计算性思维从不停息,达不到沉思。计算性思维不是沉思之思,不是思索在一切存在者中起支配作用的意义的那种思想。
因此就有两种思想,两者各以它们的方式而为有根据的和必要的:计算性思维和沉思之思。
我们说,今天人们在逃避思想,这时我们指的是后面这种沉思之思。但人们反驳道,一味的沉思冥想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飘摇于现实之上。它没有根基。它无益于掌管日常的事务。它无补于实践的贯彻执行。
而最后人们会说,一味沉思、沉溺于冥想,这对于普遍的理智太“高”了。在此遁词中只有一点是对的,即:沉思之思和计算性思维一样不是自发的。沉思之思有时要求一种更高的努力。它需要一个较长的入门训练。与任何其他的真正手工艺作品相比,它更需要精益求精。它也还必须耐心等待,像农夫守候种子抽芽和成熟那样。
另一方面,每个人都能够以他的方式力所能及地追随沉思的道路。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思想的、亦即沉思的生命。可见我们在沉思中也大可不必“好高骛远”。我们只需栖留于切近处而去慎思最切近的东西,即思索此时此地关系到我们每个个体的东西;所谓“此地”,就是在这块故乡的土地上,所谓“此时”,就是在当前的世界时刻。
如果我们准备好去沉思,那么这个庆典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在此情形中我们注意到,一种艺术作品在故乡大地上繁荣一时。思索一下这一简单的事实,我们就立刻想到在上一个世纪,上上个世纪,施瓦本的大地造就了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我们再仔细想想,就马上清楚了,德国中部以同样的方式是这样的大地,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亦然。
我们进入沉思并且要问:优秀作品的成熟不都植根于故乡的大地中吗?约翰·彼得·黑贝尔写道:“我们是植物,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我们这种植物必须连根从大地中成长起来,方能在天穹中开花结果”。

▲海德格尔的小屋
诗人想说:在真正欢乐而健朗的人类作品成长的地方,人一定能够从故乡大地的深处伸展到天穹。天穹在这里意味着:高空的自由空气,精神的敞开领域。
我们更加深思并且要问:约翰·彼得·黑贝尔所言于今日如何呢?还有那种天地之间的人的安居吗?思索的精神仍笼罩着大地吗?还有根枝强劲的故乡——人在故乡的根基中持存,也就是说,人在其中是根基持存的——吗?
许多德国人失去了家乡,不得不离开他们的村庄和城市,他们是被逐出故土的人。其他无数的人们,他们的家乡尚有可救,但他们还是移居他乡,加入大城市的洪流,不得不在工业区的荒郊上落户。他们与老家疏远了。而留在故乡的人呢?他们也无家,比那些被逐出家乡的还要严重几倍。每个钟点,每一天里,他们都为广播电视所迷住。每周里,电影都把他们带到陌生的,通常只是习以为常的想象区域,那里伪装出一个世界,此世界其实不是世界。到处唾手可得“画报”。现代技术的通讯工具时刻挑动着人,搅扰和折腾人——所有这一切对于今天的人已经太贴近了,比农宅四周的自家田地,比大地上面的天空更亲近,比昼与夜的时间运转,比乡村的风俗习惯,比家乡世事的古老传说更熟悉。
我们要进一步深思并且要问:这里发生了什么——在被逐出故乡的人那里,同样也在留在故乡的人那里?答曰:当今人的根基持存性受到了致命的威胁。更有甚者:根基持存性的丧失不仅是由外部的形势和命运所造成,并且也不仅是由于人的疏忽和肤浅的生活方式。根基持存性的丧失来自我们所有人都生于其中的这个时代的精神。
我们要更进一步深思并且问:如果情形如此,那么,人,人的作品,将来还会从荒废的故土中成长出来并且上升到天穹之中,也即升入天空和精神的浩瀚之境中吗?或者,一切都掉入规划和计算、组织和自动化企业的强制之中?
如果我们在今日的庆典中想到它带给我们的,那么我们就注意到,根基持存性的丧失威胁着我们的时代。而且我们要问:在我们的时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时代的标志是什么?
人们近来把现在开始的这个时代称为原子时代。它的最强烈的标志是原子弹。但是这个标志只是表面的。因为人们很快就认识到,原子能也可用于和平的目的。因此,在今天,核物理及其技术人员无处不在,力图实现核能在广泛的各种规划中的和平利用。权威国家(最尖端的是英国)的大型工业联合企业已经料到,核能可以成为巨额交易。人们在核交易中看到新的福祉。核科学没有袖手旁观。它公开宣布出这个幸运。于是,今年七月在玛瑙岛上,十八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份呼吁书中明确声明:“科学,这里即现代自然科学,乃是人类通往更加幸福的生活的道路”。
这样的断言如何?它源于一种沉思么?它可曾思索过核时代的意义么?没有。如果我们让自己满意于上述科学的断言,那么我们与一种对现时代的沉思就南辕北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忘记了深思。因为我们忘记了追问:科学技术能够在自然中发现并且开发新能源的根据为何?
它的根据在于几个世纪以来所进行的对一切规范性观念的彻底变革。人因此而被置入另一种现实之中。这种世界观的彻底革命完成于近代哲学之中。由此产生了人在世界中的和对于世界的全新地位。于是世界就像一个对象一般显现出来,计算性思维对此发起进攻,似乎不再有什么东西能够抵挡它们。自然变成唯一而又巨大的加油站,变成现代技术与工业的能源。这种人对于世界整体的原则上是技术的关系,首先产生于十七世纪的欧洲,并且只在欧洲。地球上的其他地区很长时期内对此并不熟悉。它对于较早期的时代和民族命运来说也是完全陌生的。

▲海德格尔与夫人
隐藏在现代技术中的力量决定了人与存在者的关系。它统治了整个地球。人类已经开始离开大地而向宇宙进军。而不足二十年的时间,随着核能的兴起,一个如此巨大的能源为人类所知了,以致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世界上各种方式的能源需求将一劳永逸地得到满足。可直接获得的新能源马上就不再像煤、油以及森林木材那样,局限于某些国家和地区。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地球上的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建立起核电站。

▲《农鞋》(梵高,1886)
如果对于物的泰然任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在我们身上苏醒,那么我们就会走上一条道路,这条道路通往一个新的基础和根基。在这个根基上,永恒作品的创作或许就会扎下新的根。
于是,以一种变换了的方式,在一个变化了的时代里,约翰·彼得·黑贝尔所言必将重新成为真实:
我们是植物,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我们这种植物必须连根从大地中成长起来,方能在天穹中开花结果。
【本文节选自《海德格尔文集:讲话与生平证词》,有删略】
《海德格尔文集》中文版总目录
孙周兴、王庆节 主编
1《早期著作》
2《存在与时间》
3《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
4《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5《林中路》
6《尼采》
7《演讲与论文集》
8《什么叫思想?》
9《路标》
10《根据律》
11《同一与差异》
12《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13《从思想的经验而来》
14《面向思的事情》
15《讨论班》
16《讲话与生平证词》
17《柏拉图的〈智者〉》
18《时间概念史导论》
19《现象学之基本问题》
20《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
21《荷尔德林的颂歌〈日耳曼尼亚〉与〈莱茵河〉》
22《形而上学导论》
23《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
24《巴门尼德》
25《论哲学的规定》
26《宗教生活现象学》
27《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
28《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
29《乡间路上的谈话》
30《不莱梅和弗莱堡演讲》

《讲话与生平证词》
[德] 马丁·海德格尔 著
孙周兴 张柯 王宏建 译
商务印书馆2018年5月出版
?
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下设哲社、文史、政法和经管四个编辑室及威科项目组,主要承担文史哲及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出版物包括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华当代学术辑要》、“大师文集”等为代表的多种学术译介和学术原创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