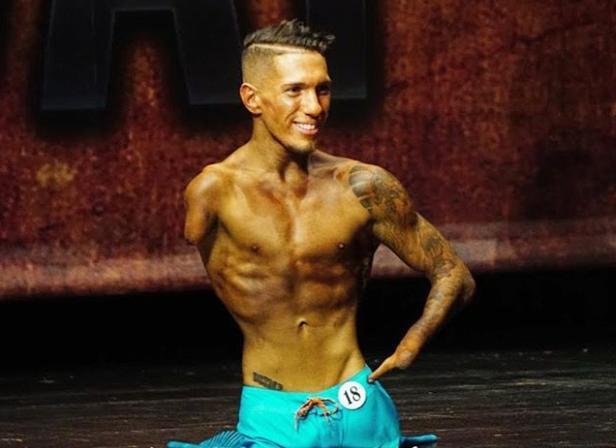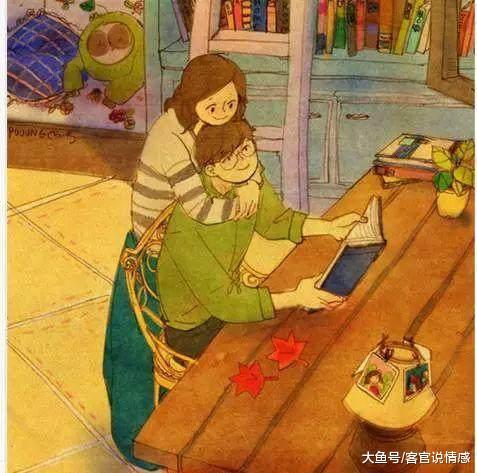班固与司马迁不同女性观的形成原因
司马迁出身史官世家。“司马氏世典周史。”他的父亲司马谈是汉的太史公。司马谈博览群书、学识丰富。司马谈不唯学识丰富,而且是个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人。他对于六家思想均有独特的看法和明确的褒贬倾向。司马迁后来写《史记》对于所记录人物常常笔端带情、褒贬鲜明,这与其父的思想及人格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既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这两句话包含着对后宫女性命运的悲叹和宽容的同情。也只有司马迁才在写史时能发自内心的对所记录人物的命运思考如此之深、感叹如此之切。

司马谈认为写史是司马氏家族所一直承负着的神圣使命。司马谈悲愤而死,只因自己身为史官而不能亲身见证汉天子“封泰山”的国家盛典。悲愤之余他只能以“命也夫”来安慰自己,并且临死时把司马氏当太史著史书的使命直接传递于司马迁。司马迁全全接受了他父亲对于著史的神圣热情。这种热情也贯穿他的一生。受其父影响,司马迁是相信天命的。正因为司马迁相信天命,而他在对于所知道的后宫女性的人生经历的或同情或感叹中始终带有一层“命”的色彩。

班固出身汉代显贵和儒学之家。他们家族仅历三代就有五位在历史中获得显名,流传后世:班捷好、班彪、班固、班超、班昭。而这五人,几乎都有其精忠的正统思想,并以或实际行为或恳切言论表现出对当时正统统治的积极拥护和热心维护。班捷好是汉成帝的一位贤妃,她自身修养极高,言行处处符合儒家道德标准,并想以此去积极地影响成帝。班彪,在光武帝时期反对院嚣割据称雄,为窦融划策,归顺刘秀政权,总西可以拒院嚣。这对东汉统一是有功的。班超胆识才智过人,其出使西域期间,使西域五十多个国家都归附了汉王朝。

班昭曾因德才兼备而常被招入皇宫,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宫中尊之为师。班固的这四位亲人都是对自己有所要求,并且有所作为的情况下得到统治阶层和众人的承认和尊崇的。班固生活在这样一个精忠正统的家族中,其思想和见识理应受到影响,也是积极而正统的。所以,他的《汉书》,无论在行文风格还是在支撑思想上更多地表现为严谨客观。他的女性观也就更实际,也就是,女性应该有为有不为、注意修养身性已达德才兼备,进而保位全家。

司马迁胸怀热情、个性秉直。正因为他对生活于其间的现实世界有着真诚的关怀,就常常忘记自己的处境去理解去维护一些处于不公平境地的人事。他所受李陵之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班固也叹道:“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要司马迁做到明哲保身是很难的。因为他是个对世界充满好奇与热爱的诗人。

所以,李陵技降,司马迁就胆敢越位言事,为他找出技降的多条理由,尽管他与李陵“素非相善也,取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可惜他汲汲于的天理公断在统治者眼中显得天真而多余。不但没有救成李陵,反倒使自己蒙极刑之辱,给自己的生命留下了永久的阴影与伤痛。
一些无过错的人受着不公平的对待,司马迁尽管想为这些人鸣不平、讨公道,无奈自己力量微弱至极,尚不能自保。处于这种苦闷中的司马迁只能以“命”去解释这些不平,去开解自己。对于后宫女性,影响她们命运的因素错综复杂、更是不可把握。司马迁无力找出是什么力量使一些女性享受荣华与尊贵,而另一些女性红颜薄命,悲苦一生。以他的性格,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只能终结于命运观。

班固自幼聪慧,“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班固喜读书,而且有对九流百家之言穷究的耐心和喜好,这和司马迁津津乐道于他的游历是不同的。相比,在性格上,班固没有司马迁那么多的豪情壮志以及对大自然的热情向往。更多地他是个博览群书后穷究学理,思想中正的人。“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家国为重,个人应当做到行不逾矩。“窃见故司空揉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从心,行不揄矩,盖清庙之光晖,当世之俊彦也。京兆祭酒晋冯,结发修身,白首无违,好古乐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时俗所莫及。”他所真心尊崇的人是善于修身、好古乐道的名儒之士。这些人性平和、内修好,不会对国家的安危治乱造成威胁,从另一角度看,也是进行了极好的自我救赎。历读无数史书的班固在看历史中的女性时,也是以他中正容众的性格、修身为重的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所以,有了不同于司马迁的女性观。

司马迁最重要的人生经历有三:广交游、著《史记》、遭宫刑。司马迁二十岁则遍游中国南北大地。在上面这段自述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这段游历也是津津乐道。以此可见,司马迁必定对地产风物、世俗风情有强烈的好奇心,对自然风光的美有超凡的感受力。所以也只有他才说出了“究天人之际,以成一家之言。”这样极富个性与雄心的话。
写《史记》,司马迁历览各代史书,眼光及思索所及上下数千年。“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记于大汉。”@广博的游历、大量而勤勉的阅读使司马迁在横向地理感、纵向历史观的积淀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独特的广阔的视野和深邃的思想。而当这些美好的富个性的特质在现实中遭遇宫刑时,司马迁的精神世界若不是靠写《史记》这一神圣使命支撑着,恐怕难免崩塌。“且夫藏获焊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己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自己毫无过错,却遭极刑受极辱。而且对此,他只能隐忍接受。他的悲观的命运观便由此形成,以其来观照不能自主后宫女性的身世经历就有了司马迁的女性命运观。

与司马迁相比,班固的人生经历就显得平凡得多。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著书了,是一种典型的学者人生。没有司马迁经历的激情壮游,也没有他的大辱身残后内心里的隐忍颤栗。一部《汉书》的传世,使班固成为伟大的史学家,他也因此倍受后人的关注和尊崇。在班固所生活的年代,他虽因学识积累和卓越文才得到当时诸学者和章帝的赏识,在仕途上却一直处于御用文人的卑微尴尬的地位。明帝时他任兰台令史,与人共修《世祖本纪》和一些列传、载记多篇奏上。章帝时,班固职位很低,是守卫玄武门的下级官吏。因为章帝赏识他的才华而常被召入宫中侍读,也常随章帝出巡并为其作颂赋。长期处于这种陪侍文人的卑微地位,班固说话办事估计都得小心翼翼才能自保。这种经历对他女性观形成的影响是直接的。
女性,特别是后宫女性也处于依附地位,在班固看来她们就像自己一样首要的任务是保全自己的性命。后来,班固又奉命参与由章帝主持在白虎观举行的当代名儒论五经的活动,并在当场整理记录他们的讨论结果,篡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这次参与儒学讨论并进行整理记录的经历对尚儒的班固来说又是一次思想上的熏陶与濡染。他的女性观也是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依据的。
本文由若雁传奇娱乐苑原创,欢迎关注,带你一起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