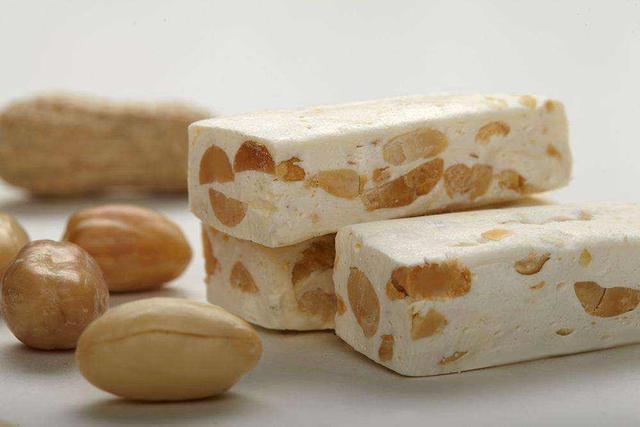宜多宾巷的孔府老宅

去年是陈从周老先生诞辰100周年,前段时间苏州园林博物馆曾有一场专题展览。笔者有幸临场参观,见到了他的传世之作《苏州旧住宅》。书中有宜多宾巷14号孔府老宅的图文记叙,图例表述之精准,实令当年的老住户感慨且赞叹不已。有介绍说,陈老先生20世纪50年代初曾执教于当时沧浪亭北侧的苏州工专,他利用每周从沪莅苏授课之隙,遍搜苏城名门望族尚存的老宅,孔宅只是其中之一。命缘天授,完成得如此之好,实属苏州之幸。
孔氏老宅的主人是衍圣公七十一代孙——孔昭晋。
据载,孔子五十四代孙思字辈以下,以“克、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字排列,苏州圣裔按谱牒朔支派系,有传、彦字后辈先后迁入木渎之南横泾(清代称横金),遂日以繁衍。
横泾孔氏第七十一代孙孔昭晋(1863-1936),字康侯,弱冠成秀才,后来迁居城中,光绪十年(1884)成为举人,十九年后光绪二十九年(1903)会试进士,数年间先后创办小学堂三十余所,宜多宾巷14号老宅应系孔老先生中晚年购得,并亲自操持修缮建设。
陈从周著述中对20世纪中叶老宅景况介绍为:“宅有照墙、轿厅、花厅、大厅等数进,西北隅小园清沼,林木森森……”老宅面巷坐北南向,占宜多宾巷13、14、17三个门号,主路14号,主路第二进花厅,高悬“进士”匾额。
孔昭晋膝下分三房居于宅中,长房居13号,二房居14号西南侧内院,三房居14号正厅及后花园花厅。17号正门厅房供作家族祠堂。
长房遗孀长寿,到20世纪80年代,仍由一孙女陪伴居住于13号祖宅第二进楼上,与邻居街坊相处十分融洽。当时有一老房客儿媳生产,住市二院产房,大房孔氏孙女还去找二院的院长、妇产科专家顾乃勤求助。顾院长百忙之中亲临病床,仔细复诊并嘱咐再三,临产时还守候在旁,终至一切顺利。过后大家才知,孔昭晋老先生有一长女嫁苏州七子山顾氏传人顾允若之弟顾仲华,顾仲华居滚绣坊26号,宅中砖雕门楼至今尚存孔昭晋所书之横额,顾乃勤是顾仲华之女,孔家孙女亦是顾乃勤的侄女。
进入宅院的路径,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仍以宅园南向宜多宾巷14号、13号、17号为主。后来,孔氏后辈逐渐散离老宅,房产遂有外人租住,租客们概由孔家人遴选,或旁系亲戚,或银行、邮政白领、米行业主等。

宅园最北端有一小门,位于马医科,标门牌为23号,之前一直关闭,直至1956年始,打开作为北向进入宅园的通道。由此,原西北隅的花园、池塘、花岗岩石板小桥、湖石假山小丘、几百年的粗高银杏才从厅堂身后,显现于世人面前。
与后花园一墙之隔,即为马医科29号的绣园。绣园的前身是清末词人郑火焯的讴园。园内厅堂廊轩池石布局精巧,但无高大树木,由绣园内举目东望,隔墙之高大银杏树,可撑足满幅翠绿金黄,凭添山野之趣,是姑苏城内中心地段不可多见的景观。
高大银杏现存有两棵,粗的一棵当年围径在二米以上,高约三十余米,树冠围径似二十米开外,罩没树下十多米的绿地,还跨上了本宅东侧花厅及隔墙绣园的厅堂屋顶上。当时春夏浓绿敝日,秋日挂果满枝,金黄簇拥中,果与叶密密匝匝,满地果实与落叶铺就,令人不忍下足。景致实在可以跟留园的“又一村”有一比。
可惜的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市内住房紧张,有人迁入,并在树下空地自建住房。这两家住户日积月累带回建材,小房逐渐变大房,平房变楼房,一点点把树下空地填满塞足。可怜大树后来已全部围在房墙之中,树干下部已不能靠近。自此以后,大树几无增长。前段时间去看老树,虽然依然虬枝雄壮威武,可惜多处梢端已枯樵散乱,不复当年的茁直生猛。
当年池塘东南处还有一小池,是三湾相连相通,池塘最深处有一石栏深井,故而池塘水质至上世纪50年代末,一直清澈而干净。
六十多年前的宅园,蛙呱、蝉噪、秋蟀鸣,夜虫一样不缺。秋末冬至,高大银杏皆为满树的累累硕果。

孔昭晋老先生社会身份颇多,身兼苏州教育会会长,吴县议事会议长、吴县教育款产经理处总董、江苏省议会第二届议员、苏州工巡捐局董事、城市市民公社社长、民国《吴县志》总纂等数职。这片旧宅的实际持有人,此后更替为昭晋先生的幼子宪镳(1899-1988)。孔宪镳,字叔慎,历任上海银行观前办事处主任、国货银行苏州分行经理,处事诚信,乐善好施。他曾遵父命,独资修茸横泾至淑庄的堤岸。苏州解放后,国货银行由人民银行接收,有关部门清点账货,发现只多不少,业绩口碑由此传颂。孔宪镳恪承家教,重视子女教育,后辈分别毕业于圣约翰、震旦等,其重教厚文之风,绵延泽被,故里租户中纷纷钦慕言传。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叔慎先生偶尔由沪上返苏,一身长衫,一副眼镜,谦谦若谷,早餐佐以一碟花生,亲见耳闻者均奉为范举。故里多家租户后辈,秉承厚学之风,50年代初首先有一女孩被录于浙大,此后一个清华,一个唐山铁道,又一个清华,一个武汉钢铁,一个南京化工,连连告捷。60年代初,又出了一个南京师院、一个大连海运,并有多位后生在苏中、师院附中、三中、一中二中等校在读。
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文革”与上山下乡的变迁,孔家老租户所剩无几。其中有一位值得一提,他便是活跃在当今世界乐坛的青年作曲家王之一。王之一出生时宅居于银杏树下西厢房之内,他年幼时就禀赋聪慧,90年代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此后又赴美深造。还有那位得助于顾乃勤院长顺利出生的小孩子,长大后也学有所成,成为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生物医药学博士。
苏州城的街巷之中,阡陌变化竟有几何,恐怕是任何人都难以说得清、道得明的。上世纪50年代,宜多宾巷附近还有多个高墩墩,分别在宜多宾巷、神道街、尚书里、桂和坊,其实都是建房开挖废土瓦砾的堆积,但高度、占地都可观,附近的人去高墩墩上放鹞子是一件趣事,可见当时城内闲地之多。后来随着城市主干道拆宽改造,以及人口越来越多,这种高墩墩一个个都不见了,场地纷纷被建房利用,住房紧张仍然不得缓解,各个宅园内的空地,也就难逃被蚕食的命运了。
上世纪60年代初,孔宅北门马医科23号,进门左侧先是造了一幢筒子楼,后来池塘被填,假山被废,又盖了一幢二层高的公寓楼。如此,主通道以西的花园池塘景致就此荡然无存。到“文革”后期,两棵高大银杏树冠下的空地也不得幸存,再遭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的搭建,大银杏侧旁的一棵小银杏也遭砍伐,两棵大树被围在房墙中,靠近不得。
犹记当年,登临城北报恩寺塔(北寺塔),远眺一片粉墙黛瓦之上的景观,孔府老宅的大树极易辨识。如今北寺塔难登,这片风景也已封存记忆久矣。

原载于2019年2月24日《姑苏晚报》A13《吴地》
来源:陈志坚/文 陶开俭/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