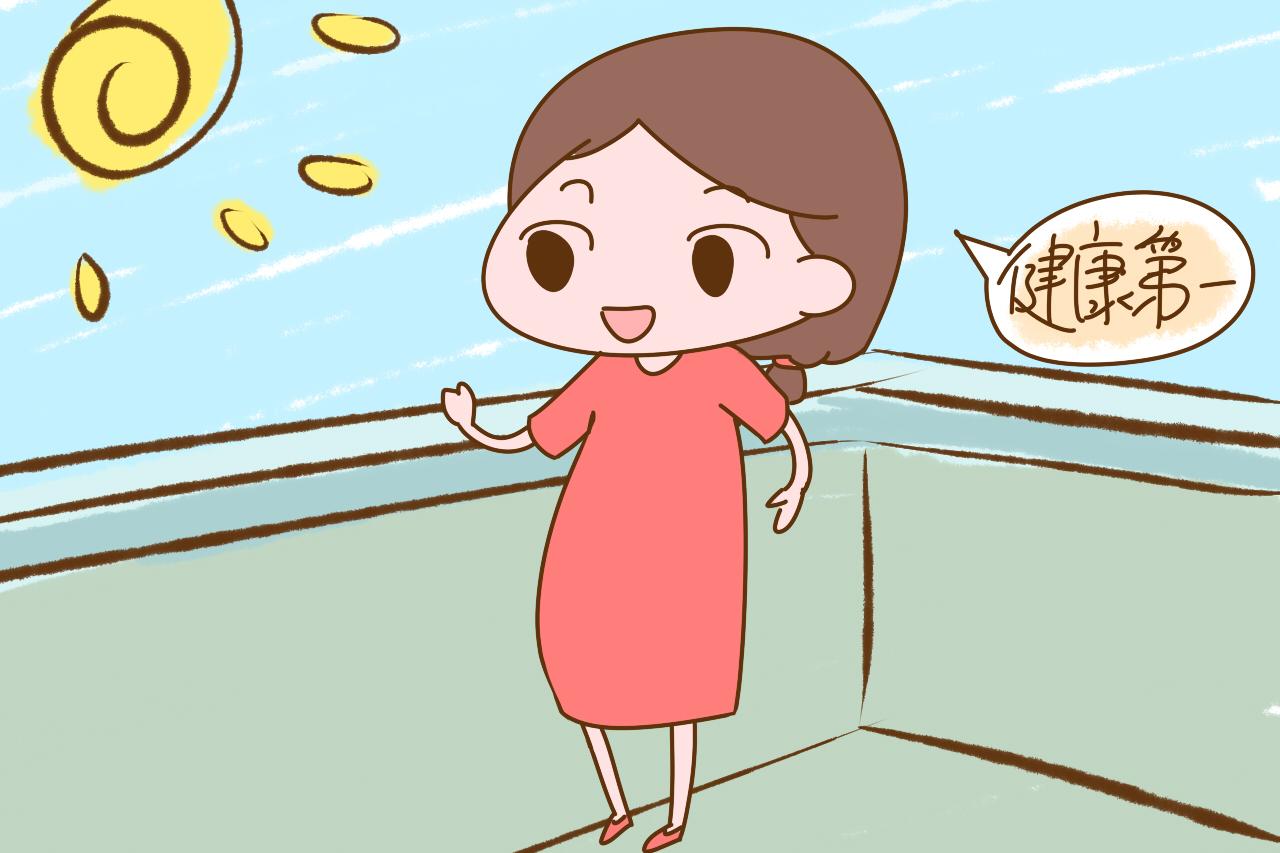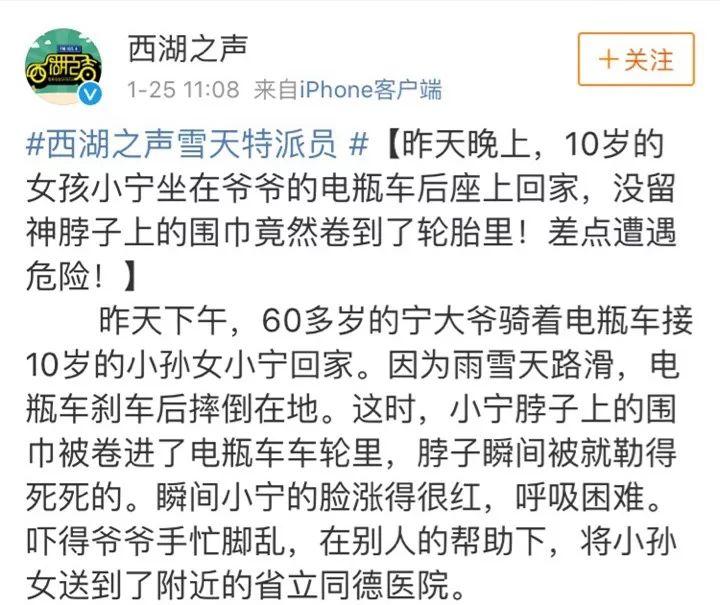在蜜蜂吸蜜的地方吸蜜

▌茱萸
陈黎与我在2015年秋天初次见面于福建的某次诗会。但更早之前,他的盛名对我而言即已如雷贯耳。当时我已读了他的不少诗,印象深刻;听说过他的些许趣闻,想见其风采;亦受益于他与张芬龄多年来对许多国外诗人的译介。
大概一年前,《世界的声音:陈黎爱乐录》出版;如今这本诗歌笔记则以《诗歌十八讲:陈黎、张芬龄诗歌笔记》的名目于东方出版社梓行,亦算得上遥相呼应。这对诗人、翻译家夫妇于诗而言固然是专业的,但与他们对音乐的倾情一样,这“专业”里的初心依然是对诗的爱。
《诗歌十八讲:陈黎、张芬龄诗歌笔记》谈到的诗人、涉及的范围极广,视野非常开阔,既有普拉斯和泰德·休斯夫妇,有聂鲁达、拉金、希尼、巴列霍、帕斯、辛波斯卡、赛弗尔特和特朗斯特罗姆这样的大师,还有卡罗尔·安·达菲这种诗坛正当年的“野兽派太太”,亦有日本的与谢野晶子和韩国李朝时期的黄真伊,甚至谈及了小诗和日本俳句。可谓熔古典、现代与当代于一炉,集西洋、东亚于一身。《诗歌十八讲》的初心与重点,终究还落实在对诗的爱,以及因这份爱而激发出的评断与分享的热情。这两层意思,非常适合用陈黎自己的诗——譬如《狂言四首·普洛斯帕罗》的结尾几句——来表达:在蜜蜂吸蜜的地方吸蜜,/在梦隆起的地方储存短暂人生……一阵音乐,给爱情以食物,/给虚无缥渺的东西以档名,位址。
那些被作者谈及的诗人从他们的生活中吸蜜,陈黎夫妇这对“蜜蜂”从那些诗篇里吸蜜,读者诸君与我,不正准备着从本书这个吸蜜的地方吸蜜吗?诗和音乐一样赋予爱情与人生以哪怕虚无缥缈的意义,因此成为食粮,在世界中获得了它的位址。
总的来说,《诗歌十八讲》里的文章不同于一般的鉴赏之作,篇幅并不短小,反而洋洋洒洒,多以长文呈现,有相当之丰富与专业性。所谓“十八讲”亦并非两人的一时兴起之作,并非为某类诗歌讲坛特撰的专题讲义,实质上是他们历年翻译的诗集的导读或译序的结集。对读者诸君而言,这部诗歌笔记可谓是一场“理解诗歌”的盛宴;对于讲诗的作者而言,则是他们译诗、解诗的劳作之余,和无所不在的倾听者与注视者展开的对话,而不是单向度的讲演或高谈阔论。这种对话,是劳作间隙的休息和公共空间的私语,是犹如“摆渡”和“为他人做嫁”的翻译行为的伴生物。但更重要的是因熟悉而娓娓道来、因专注而心无旁骛、因与人分享而有所奉献的热爱。
我曾在书评里称陈黎为“来自宝岛台湾的花莲土著”,说他在文学艺术领域涉猎非常之广,包括诗、翻译、乐评与散文。陈黎的著作出现在大陆阅读市场,要早到世纪之初,不过当时出版的两部作品美则美矣,谈不上是“诗人陈黎”的当行之作:《夏夜听巴赫》是关于音乐的随笔;《百科全书之恋》列入“港台名家书话文丛”,虽涉读书、观画与聆乐,终归不过为当年的“书话热”锦上添花一把。
他去年出版的那部爱乐录,同样算是客串。要说当行,在我看来,除了个人诗选之外,本次以随笔体写就结集的这本诗歌笔记,才是最符合诗人职分的一次呈现——他们的译者身份只是表象和由头,作为诗人的陈黎对不同语种和各色风格的诗人的理解和阐释才是重头戏。毕竟,同行的高手之间,知音难求。
藏在本书后面的两位作者,此次虽然书被冠以“十八讲”之名,但依然不是以批评家的身份发言的。陈黎夫妇在台湾是非常资深的翻译家,是宝岛上最早致力于译介拉美诗人的译者,但他们在内地声名鹊起大概是到2010年以后了。这些年间他们作为翻译家的成果引人瞩目,而与这些成果伴生的译序和谈诗随笔如今就这样地结集于此。我不知道会有多少读者冲他们作为翻译家的名气来买这部书,但我认为,无论翻译还是阐释,无论热爱还是专攻,他们所有的这些文化劳作皆围绕着“诗人”的身份而展开,所有的认同与荣誉亦都比不过“诗人”这顶冠冕的分量。陈黎诗选《蓝色一百击》去年出版后,我在为之撰写的书评里这样说:“陈黎首要的文化身份是‘诗人’,而非近几年风靡大陆阅读市场的‘著名翻译家’或颇具标签色彩的‘辛波斯卡译者’。后两者的头衔或角色,在普通读者那里如今远比‘诗人’的身份更能收获欢迎与尊重。但倘若我们的视野能够更广阔一些,就能发现,陈黎真正的、更能传之久远的声名与影响力,或许还要落实在他的诗的创作领域。毕竟,无论大名鼎鼎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还是洪子诚、奚密等精心编选的《百年新诗选》,对其‘语言与形式上的魔力’的首肯,以及‘丰富多元’‘杂糅’与‘标新立异’的赞许,皆本于对其诗之创作领域的认定。”
我这么说的用意,并非指陈黎诗之外的文字就不重要。恰恰相反,这些与诗有关的不分行的文字,是他“真正根基”背后的养料与来源。这部诗歌笔记之所以有理由成为上好的谈诗文字,亦不仅仅因为这背后有热爱,最关键的是,这热爱来自于“诗人”。与批评家或学者蝴蝶炫翅般的高谈阔论相比,诗人用细微的语调谈诗,如蜜蜂发出嗡嗡的声响——他们总是更清楚语言之蜜的真正位置。(引自《诗歌十八讲:陈黎、张芬龄诗歌笔记》序,有删节,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