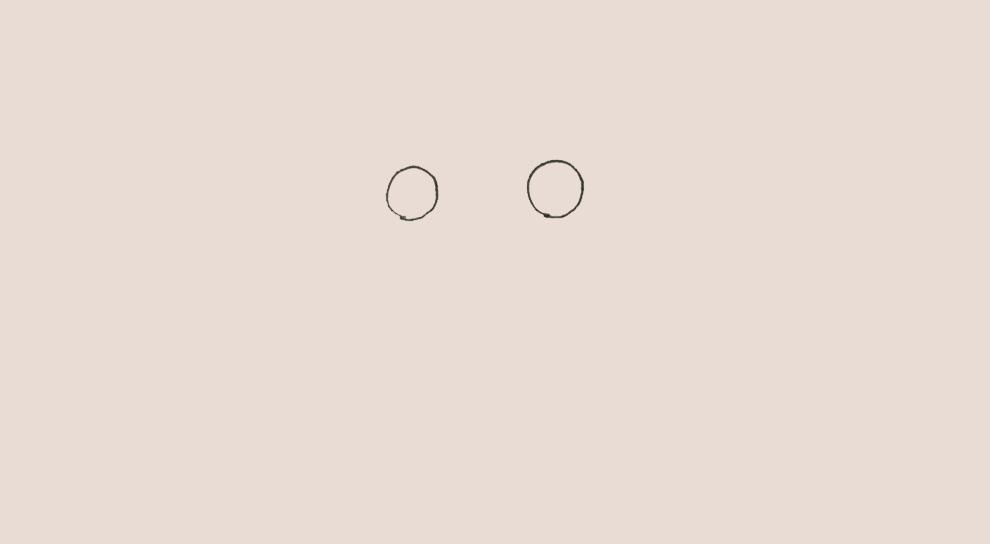我与书籍的故事
我与书籍的故事
文 / 谢清扬

回忆起关于书本的记忆,总是十分清晰且印象深刻,恍若再次掉进当年读的故事书里。
几年前,弟弟还未出生,妈妈也不忙,一家人有兴致耐心坐在一起开个什么“会”。那天晚饭后,在东边的卧室里开会。讲台是距床尾一米多的电视柜旁,不远处还有一筒紫色的塑料花。一家五个人分散坐在床边或板凳上。我一个小孩子,当然异常兴奋,且自认准备十分充分。我第一个上场,捧着一本《爱的教育》。这本书是借的,扉页上还写着“八百标兵奔北坡”的绕口令,里面的故事我印象极深(可能是带了黑白插图的缘故)。我的准备工作就是在字里行间找出孩子抱怨家长的话(殊不知那是做反面教材用的),因为觉得自己的话上不了台面,便借用它洋洋得意地大念起来。念毕,妈妈的脸色不对,说我不该这么说。我委屈得要哭。我似乎就是在自信不断被打击的过程中成长的。“会”后,我被迫郑重其事地写日记,勉强写了一页。那本《爱的教育》没有还回去,估计在某次捐书中捐了。

半大的小学生似乎都沉迷在《怪物大师》和《查理九世》中。被问及最喜欢什么书,我和同桌异口同声:“《查理九世》。”在一个地下书店里,我有了第一张借阅卡。那是个很昏暗的地方,书架很满,一排排紧挨着。一整套《怪物大师》就是在那里借出看完的。当时因为看了这些可怕的故事,很怕黑,碰巧通向图书屋的楼梯黑得昏昏沉沉,墙壁后一间厕所,风一吹,门就吱吱呀呀地扭动。但我还是怀着恐惧而又兴奋的心情朝书架上昏黄灯光下的故事书走去。直到寒假过后,书馆关闭,我借的最后一本沈石溪的书一直保留在家里。当然,30块钱押金就留在借书的地方了。后来这本书也被当做旧书捐出去了。
我小的时候,妈妈从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好妈妈。但有一次她把自己写的一篇文章投在了我们学校的校报上,并且获了奖。记得领奖时,妈妈特意穿了黑色花纹的短袖,牛仔裤,披了黑色开衫。我在台下队伍里得意地笑。奖品中有方圆书市的借阅卡。爸爸抽空带我去借了第一本书。那三排长短不一的书架围起来的,真是一个琳琅满目的世界。我仿佛被吓着了。在众多书本里,我很严肃地挑了本《淡白的古果》。当时我并不理解书名的意思。前台阿姨登记时,礼仪性地装作很了解地说这本书不错。看完知道,淡白是个女孩儿,古果象征着她那个年龄苦苦追寻并最终得到的东西。

那段时间,对借来的书真是到了痴迷的程度。记得很清楚,是一本《木棉离歌》,写完作业,双腿蜷在书桌旁的大皮椅子上看。那真是妙不可言的时刻,自己仿佛到了书本里,与主人公同笑同泣,魂儿被勾走了一般。现在很难有那样的体验了。
六年级,心智发展,有了一些女孩子独有的敏感。恰好,班里一些成绩好的潮人开始往班里带小小姐的书。各种女孩儿被画得楚楚可爱,每一本书的封面都无一例外地吸引着我们的心。或许那时的我们都向往那个样子。另外,还有各种漫画,《妃夕妍雪》《穿越西元3000年》,无一例外的浪漫故事。我们就在这粉红色调滋润下,上了初中。
初中书读得很少,闲一会儿便想去玩。暑假国学班读书会,我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一本可以拿得出手的书《追风筝的人》。那次读书会,我顶着个锅盖头,穿着蓝上衣,蓝裤子,站在该站的位置,很紧张地念稿子。

那时的我很不自信,加之相貌丑陋,总觉得没什么值得记下的,或是因为时间太近,觉得还未走出当年的影子。但那是段快乐的时光,好朋友都在。一起做游戏,一起分享,很快乐。
再想想最近,关于读书的记忆更少。但总的来说,这次笔路上,我走得十分流畅,这或许是写回忆的独有的特点,要是我老了,戴个老花镜,写我关于书本的故事,能记下来的比这多得多,那就好了。

? END ?
作者简介:谢清扬,女,二00五年出生。名字取自《诗经?郑风》“有美一人,清扬婉兮”。现就读于正阳二中。喜欢读书、收藏、旅游,希望用文字记录生活。
本文为"等你FM"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