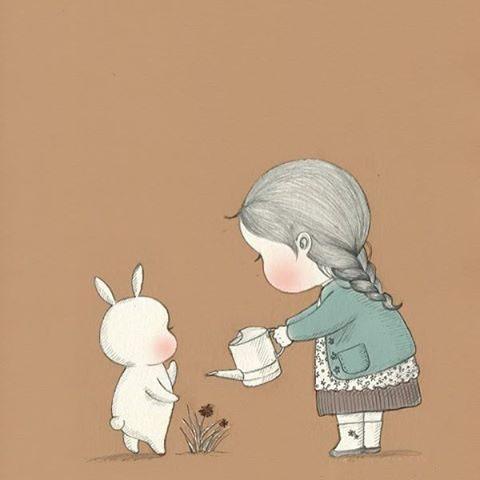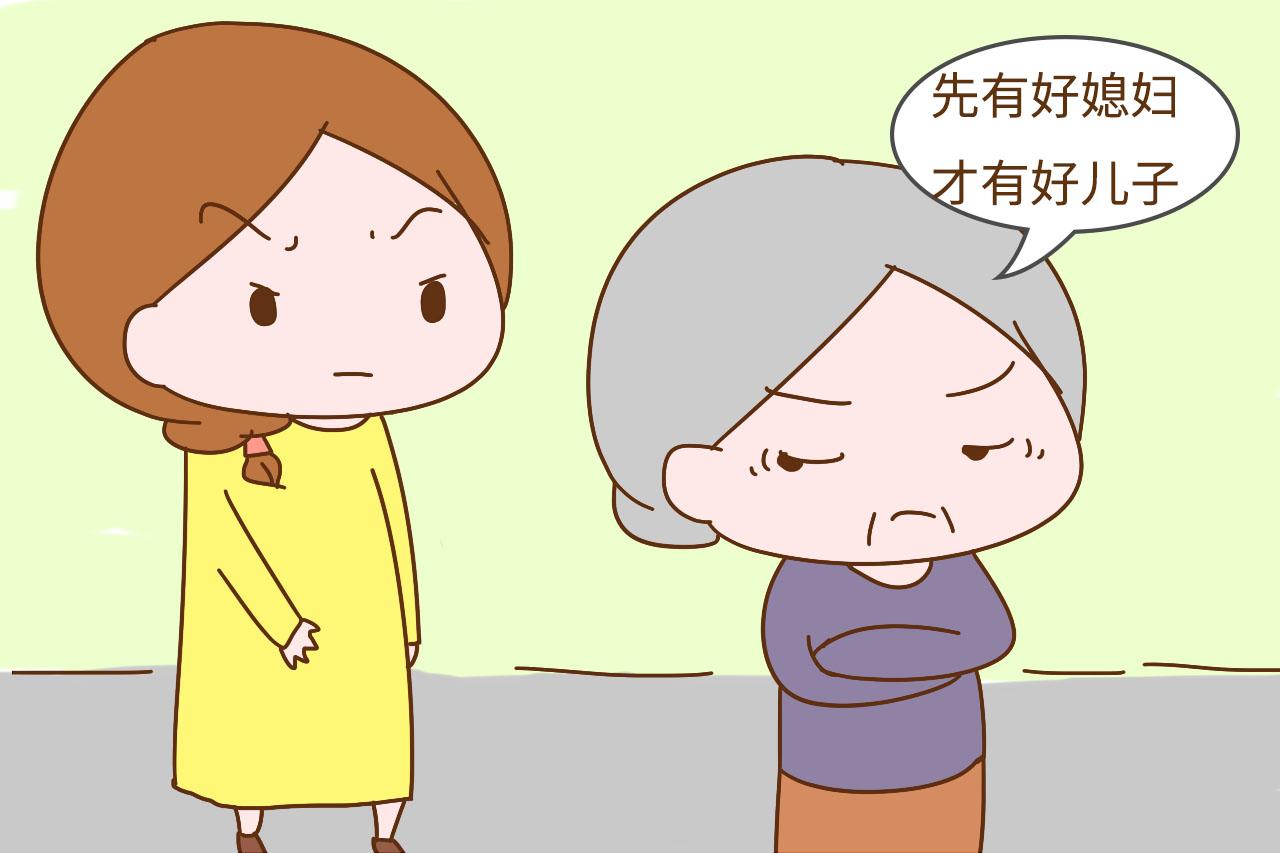相亲成功概率小 但他们还是风雨无阻来

他们的穿着打扮暗暗用力
“服务员,帮我拿只纸杯。”
这是2018年11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四,下午2点,在宜家家居徐汇商场二楼的餐厅里,接连有阿姨爷叔拿着会员卡来到收银台。
“这两天商场搞活动,免费咖啡没有噢。”服务员指指柜台上的告示牌,打招呼说。
因为是工作日的关系,餐厅里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不多,六七成是中老年人。
免费咖啡不供应,2块钱一支的双色冰淇淋蛋筒大受欢迎。放眼望去,不少阿姨爷叔都在啃蛋筒。
有些爷叔两手各举一支蛋筒,笑盈盈地走过来,自己吃一支,再递给旁边的阿姨一支,空气里有一种轻松欢快的氛围。
乍一看,这些阿姨爷叔没什么特别。但仔细端详,他们的穿着打扮可是暗暗用力的。
阿姨大都略施粉黛,秋意渐浓风愈凉,但穿裙子、蹬高跟鞋的大有人在。金秋季节,这里的时尚是在脖颈系一条空姐范儿小方巾,搪风保暖又好看。
染发的也不少。还有一位高个阿姨一头栗色俏皮短卷发,只是一转头,耳后露出一截灰黑色,原来是戴了一顶假发套。
爷叔呢,纷纷穿上衬衫,钮扣系到领口,平添几分正式感。更考究的套了西服打了领带。
大家的“dresscode”(着装标准),参照的是请客吃酒、同学聚会这样的重要场合。因为每周二和每周四,不少人是抱着相亲交友的目的来到宜家餐厅的。
阿姨爷叔三三两两坐在各处,有的小姐妹扎堆,有的男女混坐热闹成一团。有的点了餐厅里的餐食,有的手拿一个保温杯,从包里掏出水果点心巧克力,一一摊在桌上。
那边有爷叔刚到,相熟的人跟他打招呼。
“侬哪能(怎么)才来啊?”
“早上起来已经7点多了,买菜烧饭,忙得不得了,还有空到此地来?”
这边三位爷叔正在聊天,一个染红发挎红包的阿姨风风火火走过来。她不坐爷叔旁的空位,而是背对他们坐下来,但又转过头去跟其中一位爷叔聊天,姿态若即若离。
“这个人就是我上趟跟侬讲的,67岁,阿是蛮后生(年轻)的?”阿姨把手机递给爷叔看。
“我今朝做了小菜带给侬吃。”聊了一会儿,阿姨故意轻描淡写地说。
“我不要。”爷叔不领情。
“我特地带来的。是我做得好,还是侬做得好啦?”阿姨对自己的厨艺颇为自信。
“当然我做得好。”爷叔不解风情。
“侬这个怪人!不跟侬讲了,伊拉来喊我了。”阿姨被无情拒绝,只好找借口走了。
有几个“单吊”的老爷叔,背着手在餐厅里缓缓踱步,寻找合适的圈子加入。其中一位身材瘦削的犹豫了一下,在两位并肩咬耳朵的阿姨面前坐下来。
大家交谈了一阵,阿姨亮明态度:“我自己有钞票有房子身体好,要求对方条件也要门当户对。刻意去寻,是寻不到的。就在此地讲讲言话吧,消磨消磨辰光。”
“独居老人太孤独了”
餐厅的大玻璃窗边,有一排吧台式的高脚座椅。一些成对的阿姨爷叔喜欢肩并肩坐在这里,看着窗外高架、轻轨的车来车往,细细倾谈。
坐在高脚椅上的方爱玲(化名)看我在找座位,友善地指指她身边的一个空位说:“这边没人。”
她一头齐耳短发,人有些瘦弱,没有刻意打扮,笑起来很和气。
在她另一边,坐着小姐妹。此刻,她们俩索性转过身子,正对着餐厅里分贝渐高的人群,只是眼神有些茫然。
“倷住了啥地方?”忽然跑过来一个戴白色鸭舌帽的老爷叔。
“阿拉天山的。”小姐妹代为回答说。
“噶巧啊?我认得一个人,住天山电影院附近。侬几几年生的?”
“(19)53年。”小姐妹看看方爱玲说。
“噢,来事(可以)呃。他是(19)49年。房子也有,71个平方唻,老大的。”老爷叔说。
“不是我寻,是她。”小姐妹指指方爱玲说。
“不是侬啰?侬不寻啊?”看小姐妹摇摇头,老爷叔对方爱玲说,“个么侬留只电话号头(号码)。他等歇(等会儿)大概来的。要是不来嘛,夜到通只电话好伐啦?”
方爱玲回了一句,见老爷叔没听清,小姐妹又代为问道:“她问,人哪能(怎么样)啊?”
“人可以的呀,接下来就是谈吐适宜(舒服)不适宜的问题了。”老爷叔很有经验地说,“人再好也没用偿,谈吐不适宜也会崩脱呃,没缘分嘛!有缘分就谈得拢。没缘分的,两个人话也不讲,急死人了。”
“侬蛮好心噢。”小姐妹说。
“嗳,我跟他熟悉嘛。一般不熟悉的我不管的,这种事体吃力来兮的。”老爷叔摆摆手,又力劝方爱玲,“侬留只号头,不来事嘛一记头崩脱,不好勉强的。”
方爱玲写下电话号码,老爷叔匆匆走了。
我在旁边竖着耳朵“偷听”多时,有些犹豫要不要借此机会跟阿姨们搭话。
没想到方爱玲主动回过头来,像是解释似地对我说:“阿拉不认得的,他是在做红娘。”
她指指身边的小姐妹:“这是我朋友。她有老公我没有,她陪我来的。阿拉是头一趟过来。”
她又问我:“小姐侬过来吃咖啡啊?”
我抱着谈话可能即将终止的心理准备,老实地亮明了身份和来意。好在她非但没有表现出戒备和反感,反而很高兴能在这里找到人说说话:“阿拉此地一个人也不认得,老戆噢。”
她告诉我,丈夫前些年生病去世了。她有很长时间走不出来。“要得忧郁症了。阿拉儿子把我接过去,我有两年辰光基本没出门。”
等心情平复些,她“溜”回了天山的老公房一个人住。“我想呢,小孩有小孩的生活观念,阿拉老人有老人的。伊拉'哇啦哇啦'要讲小孩伐?我总归肉麻(舍不得)的。”
几个要好的邻居劝她“再寻一个”。“我讲我不寻,现在男人没好的,人都很自私的。”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开始为将来担心。“现在老邻居在一道还好解解厌气。”她说,“但是这个房子呢,旧是老旧了,住得不适宜。”
她既期盼着住房条件尽快得到改善,又有些忧虑拆迁后的生活。
“假使下趟(今后)房子拆脱了,我也老失落的,一个人住不放心。”她说,“现在还不觉得,等再老一点,走不动了,就想有人可以帮侬搪脱一点了。我有心脏病,万一生毛病,身边没人总归老讨厌的。”
儿子是孝顺的,叫她搬过去一起住,但她不忍心增加儿子的负担。“他丈人现在身体不好,小中风,他又要管小孩,所以压力老重的。我尽量把身体保重好,不去麻烦阿拉儿子。”
于是,她想着要不找个老实本分的人,大家一道过过日子。“有些男同志会做的事体,阿拉不会做,比方讲修修弄弄。我现在拎米也拎不动了,只好每趟买一两斤米。”
“有亲戚朋友会帮忙介绍吗?”我问。
“人家不敢介绍,这事体老麻烦的。”她说,“因为阿拉这个年龄都有小孩,房产上都写自己跟子女名字的。我听人家讲,有的人谈(恋爱)了,小孩晓得了,跟爷(爸爸)讲:侬结婚可以,房子卖脱,一人一半。谈到后头就崩脱了——侬房子卖脱,个么结好婚待哪里去?不管我有没有房子,侬总归要有房子啰,对伐?”
她这次来宜家,是听邻居介绍的。“小区里两个老太厌气没事体做,经常到此地来吃咖啡,讲这边有老年人来寻朋友。”
“伊拉讲:侬要多去几趟。假使只去一趟,没噶巧的。”
她和小姐妹1点半就到了。观望了两个小时,她的体会是:“我下趟不来了,伊拉都有圈子的。”
说到这里,她张望了一下餐厅里的人群。戴鸭舌帽的老爷叔一直没有再出现。“不要是骗子噢?”她说。
小姐妹看看手表,提议说:“阿拉到4点钟回去伐?前头有几爿商店打折头,阿拉去看看,再乘车子回去。”
方爱玲点点头,又回过头来对我说:“我跟侬讲讲开心唻,就是没寻到也蛮开心的。侬帮阿拉反映反映,独居老人太孤独了。”
“我有几个小姐妹,都没老公,大家一道谈谈苦经。生毛病了,屋里厢又没人,要自己先撑起来,烧好弄好才好躺下去……就这个问题。”
“阿拉单身的人,好一道讲讲。对其他人,阿拉不讲的。苦在肚皮里,讲了人家不理解的,没体会。”
“碰到人家夫妻吵相骂(吵架),阿拉就讲,侬还有这个福气,像阿拉没这个福气。几十年下来了,小孩成家了,现在正是享福的辰光,要珍惜。”
临走前,方爱玲亲热地抱了抱我,想了想说:“侬假使看到那个老爷叔,叫他电话夜到8点钟以后打过来,或者明朝白天打噢!”
“老年人考虑得更加多”
另一天下午,我在餐厅里呆呆地坐了一个小时。咖啡和蛋糕都吃完了,还是没有鼓起勇气来跟任何人“搭讪”。
大概是因为像我这样硬是挤在阿姨爷叔堆里的年轻人比较少,有几个四处踱步的爷叔经过我的座位时,都忍不住要看我两眼。
眼看着时间一点点流逝,我终于硬着头皮站起来,走到丁瑞安(化名)面前。他穿了件深色夹克衫,看起来比较面善,此刻坐在外侧的高脚长桌边,正在把最后几口酸辣汤送进嘴里。
听我介绍了来意,他很大方地请我坐下。
丁瑞安今年82岁,退休前是高级工程师,自从5年前听人介绍宜家餐厅有老年人群体后,几乎每周二和每周四都会过来坐坐。
“我呢,有老婆的,但是过来谈谈养老问题。”他说,“有的单身的呢,是来此地找伴的。各种情况都有。”
这些年,来宜家相亲、交友的中老年人一直保持着相当的规模,最多时达到五六百人。
12年前,第一批来宜家餐厅交友的阿姨爷叔可能并没有想到,这个自发的相亲角竟然延续到现在。
那是2007年,宜家家居宣布了一项营销策略:周一至周五,凭会员卡可免费换取咖啡。
一些阿姨爷叔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条信息,接踵而至。很快,一个以相亲交友为目的的群体在宜家餐厅自然生长起来。每周二和周四,成了他们固定的聚会时间。
2013年,复旦大学社会学硕士刘承欢在宜家餐厅对阿姨爷叔们进行了一系列访谈。他把访谈内容和自己的思考写进了毕业论文《弱关系网络下中老年人的社会交往——关于万达广场舞和宜家聚会的实地研究》。
阿姨爷叔们为什么爱去宜家“寻朋友”?在刘承欢看来,这是因为“我们上海这个城市经济比较好,中老年人喜欢有些腔调的东西。宜家有宽敞、明亮、舒适且功能丰富的休闲环境,满足了上海这群中老年人对腔调的追求。”
从社会学角度看,他认为:“这实际上提醒了我们,上海作为一座超一流的城市,有关方面需要关注到中老年人一些更高层次的需求。”
在和阿姨爷叔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
“我跟他们聊下来,感觉到双方的诉求明显不在一个层面上,供需完全失衡。”他说。
“比如,七八十岁的老爷叔要找六十岁以下的阿姨,又有很强的大男子主义,要找到的人靠谱、愿意做家务,还附带了一些住房条件。从阿姨的角度来讲,如果她们满足这些条件,对男方的要求也比较高,怎么会来找你呢?”
一位老爷叔用一句话总结了宜家中老年人的相亲观:“许多人只想获得,不想付出。”刘承欢发现,阿姨爷叔的恋爱,实际上是围绕房产和钱展开的博弈,最终没有几个赢家。一位阿姨自己也说,在这里成功配对的概率是“千分之一”。
然而即便如此,阿姨爷叔“依然不论春夏秋冬,风雨无阻过来聚会”。究其原因,刘承欢认为,这些中老年人实际上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认识但不深交的弱关系网络。
“这种关系非常弱,但你又不能把它忽视掉。”他说,“这个网络更重要的是承担着为这些单身的中老年人提供排遣寂寞空虚、进行社会交往和沟通的潜功能。”
“对他们来说,相亲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刘承欢说,“重要的是,在那个年龄段,在人生比较孤独的时候,你走出来了,接触了一个比较大的群体。事实上在这个群体里,即使不做任何事,都可以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