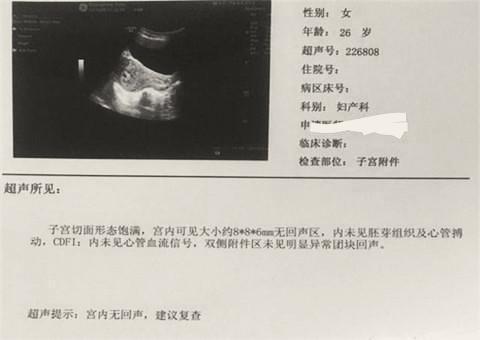今天为什么要读巴霍芬?

雅典陶器上戴着头盔手持盾牌的女人
不理解古代就无法理解现代:母权制被证实只是学术神话,却是众多现代思想的源流。
宗教人类学中有三个学术神话,即弑君的神话(《金枝》)、母系社会之存在的神话和杀父娶母的神话(俄狄浦斯),它们分别指代君臣、夫妻、父子关系这三个哲学命题。有学者认为,这三个神话主导了20世纪西方社会的文化和政治想象的走向。在这三个学术神话中,母系社会之存在神话的浓墨重彩的起笔是由巴霍芬写下的。
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代表作《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高度评价了巴霍芬的《母权论》,他是这样说的:“家庭史的研究是从1861年,即巴霍芬的《母权论》出版的那一年开始的……他(巴霍芬)头一个抛弃了关于毫无所知的原始的性关系杂乱状态的空谈,而提出古代经典著作中的许多证据来证明,在希腊人及亚洲的许多民族中间,在个体婚制之前,确实存在过这样的状态,即不但一个男子与几个女子发生性的关系,而且一个女子也与几个男子发生性的关系,都不违反习俗……诚然,巴霍芬并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述这些论点,但是他证明了这些论点,而这在1861年是一个完全的革命。”
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的人物,巴霍芬的大名在中国学界如雷贯耳,其著作却读者寥寥。此次三联书店的“古典与文明”丛书收录此书,可见编者对其情有独钟。2013年,我曾在大学课堂上亲见吴飞教授讲到此书时目光炯炯、神采飞扬的样子,也便更加理解他所说的《母权论》这么重要的著作,竟然到1973年才有了英文节译本,2007年才有英文全译本,中文译本更是到了2018年才面世,何等令人扼腕叹息。
巴霍芬出生于瑞士巴塞尔一个富庶家庭,曾先后在巴塞尔、柏林、巴黎、伦敦和剑桥学习法律和法学史,后来被巴塞尔大学聘为罗马法教授。他还长期担任巴塞尔刑事法庭的法官,但令其流传千古的,却是一份“兼职”——独立学者。
身为法学家,巴霍芬凭借敏锐的直觉,感到罗马法中的一些习惯法不可能产生自父系社会的罗马。为了论证这一假设,他前往意大利、希腊等国,以完全不同于当时主流的正统理性主义历史观的史学研究方法进行考察,并逐步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
巴霍芬在此书中第一次提出了母权制的概念,并论证了母权制在人类历史上的存在。尽管后来证实母权社会并不存在,但他的研究方法影响深远。他认为,神话传说不完全是虚构的,而是古代社会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印记,可以通过解读这些神话传说来一窥前世,“神话即历史”。
巴霍芬通过大量介绍引用吕基亚、雅典、利姆诺斯、埃及、印度、莱斯博斯等民族的神话传说与历史文献,巴霍芬向读者展现了母权并非某个民族或族群特有的现象,而在史前人类社会普遍存在,是人类早期所经历的多个文化发展阶段中的一个,并且晚于群婚制、早于父权制存在。他认为,母权代表了更加自然的生存法则,是物质性的权力,而父权则是精神性的。
在巴霍芬之后,英国的人类学家麦克伦南、斯宾塞,美国的摩尔根都发展了母系社会的学说,并将其发展为一个系统的对古代社会的表述。中国学者也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民国时期出版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李玄伯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都涉及对母系社会的描述。及至今天,对边疆民族稍有了解的读者还能说出摩梭人作为母系社会曾经存在的佐证。
但严格来说,上述学者只承认了母系社会的普遍性,但并不是母权论者,即不认为母系社会中的社会权力在母亲一方。比如在摩梭人的家庭中,虽然没有“父亲”这一角色在行使权力,但“舅舅”实则在代行父权,这样的家庭结构对于渔猎传统的民族而言,更能提供“稳稳的幸福”。
既然母权论已经被证伪了,今天为什么还要读巴霍芬?这个问题是吴飞在《母权论》中译本前言中提出的。北大教授王铭铭认为这篇前言写得极好,读者可以通过这篇短文迅速得到巴霍芬思想的深邃,并且理解母权论对现代哲学传统的影响。简言之,巴霍芬的母权神话,不仅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哲学家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也与霍布斯、黑格尔等人的现代哲学传统有着极为深刻的关系。读巴霍芬,就是要理解古典思想是如何影响西方现代文化的。
(《母权论》,[瑞士]约翰·雅科多·巴霍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